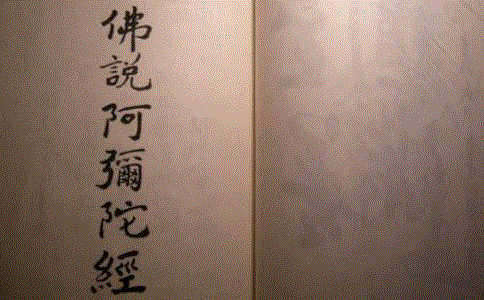斌宗大师略传
发布时间:2022-03-23 10:14:02作者:阿弥陀经全文网
皈依弟子 郑焜仁 敬述
上人圆寂年仅四十八岁,没写他底自传,诸弟子也不曾详细地记下他底生平事迹。
本文是根据遗作,及笔者所知,简要地叙述而已。 上人俗姓施,名能展,民国前一年(辛亥)二月初五,降生于台湾鹿港。其先世祖父为当地巨富,父昧目公为当代名医,文学德行亦称于世,上人少时智慧超人,五岁时就有成人的智慧,能教化同阵的小朋友行善,诸恶莫作。天资超人,坐立端正,品性良好,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六、七岁时,已通粗浅文字,喜读经书,吟诗。
年十二,始正式受教于私塾,但教师所教有限,深感不足。是时书塾对于学生系个别教授,因此购买许多不同类的书籍,当教师给同学讲解其他课程时,则虚心旁听,所读科目甚多,文、史、诗、词、均有之。上人极用功,读书不分昼夜,往往因之过度疲倦,有时甚至体力不支而伏在桌上假睡。如是一年,所学多常人数倍,且较诸正式授课的同学精通,常为同学师。
是时有一年较长的同学学诗,上人也旁听,约学半年,一日,同学求其师题诗扇上,师以事尚未顾及,上人乃作:“绿柳萋萋淡月幽,清江曲曲抗汀洲,平沙一片万余里,静夜无人水自流”一诗,以和扇上秋月美人乘凉柳树下佳景。教师惊其神慧天才,嘉奖赞美至极,此后倍加热心指导,上人学问更是一日千里。 十四岁那年春天,一日,遇一买卖古书者挑担许多书籍从门前经过。上人素极爱好古书,乃唤住该书贩,观其书籍,多为前所未闻未见者。原是一佛寺废去,经典佛书被拍卖,书贩所卖者多为佛教经典,上人以好奇而购之。从那经典得感悟世间无常,深感「功名富贵浑如梦」(上人十四岁时作七言诗中之一句),乃发出家学佛,救度众生之宏愿。又念割台事及其后经过,更证实世界上的「无常变幻」。
上人由是曾要求出家,但未得其父之许可。这时追求真理之心愿已坚决,于是有一天上人逃走到法云寺,家人因念年纪尚小,不甘其受出家生活之「苦」到处寻找,终被追回。
回家后,被禁于楼上,但日常生活已宛如出家人,维持素食,谨守戒行。日读经书,禅坐,对佛学更加了解,出家心志弥更坚决。又因当时一片清净童心,无烦无碍,学禅甚易,往往一坐数日,朗然虚空境界。
四月初七夜,上人用绳索穿过屋梁,将其一端系于一件笨重的家俱,引其另一端,乘家人已入睡的时机,安全地从楼上坠下,逃往狮头山礼闲云禅师出家。其后也曾漫游全省较有名的佛教胜地,如大湖、观音山、五指山、冈山等处。 十七岁的那年,因种种因缘,上人决定结茅独居于汴峰(台中市郊头汴坑)。每日授课学生以维持自给的生活,不愿受友人或信士的供养,也不接受馈赠。有时柴米皆尽,乃先向学生借用,及束修时照数退还。那时有一信士金山夫人(即后来狮头山海会庵第一代住持比丘尼达明师),曾以大量米粮供养,上人不受而退还之。
山居物资生活,往往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要求,但上人却过着乐道的生活。任何语辞难以说明此时的情况,但如以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比当年上人的汴峰生活,则是最恰当不过的。
结茅汴峰计六年(十七岁到廿三岁),此时授课外,尚自己用功研究法华、楞严诸大乘经典,后来也曾授信徒以大乘教义。
当时,与上人往来诸友,大都为文学界学者,有王了庵、陈仲衡、王德修、施梅樵等诸士。除了自修讲学外时常应诸士之邀,谈诗,或击钵联吟。在台中文学界诗会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人;席上如无上人在,则盛况失色,所以诸士常说:「如不往头汴坑抬下时钟(诗僧,台语与「时钟」音相似),则不知时(诗),事不能为也」。遗著「烟霞吟稿」则此时所作。 当时台湾佛教,几乎仅限于「做佛事」,僧尼对于经典大都不求了解,甚至不知「行」为何物。当时所谓「说法」不过是世俗因果报应之类,或佛教故事而已。三藏经典只见陈列,而不为四众所知解。僧尼虽诵佛经,但大多数仅是盲念,并不解佛法真实义。至于信仰更是混乱,完全不知正信与迷信之分。佛教徒甚至礼拜神鬼、外道,或与神道邪教合流。
上人悲叹海角孤岛的台湾,不得大法师指导,乃发心前往祖国留学,求法。同时渴望礼拜名山古刹、菩萨圣迹,参访高僧大德。
民国廿二年春,决心内渡,虽是贫僧,但贫穷无法阻止向上心愿。上人不愿化缘或求助于友人,甚至不受诸友送行,悄然离开茅房,但留一诗以别骚坛诸诗友。离开汴峰时,仅有一知己信徒发觉,乃赠十元为旅途之用,这对于一贫僧而言,却是一大笔的数目。
离开基隆港到厦门,从此开始参拜名山圣迹。 初渡大陆后,上人在福建游学,先游鼓山涌泉寺,在此期间曾参访虚云老和尚,且曾与虚公老和尚暨宗镜心月二师同登屴崱峰。上人早有参访古月和尚之念,但不幸来时师已西归,乃吟诗念之。此外,曾与会泉法师等同游鼓浪屿,亦曾谒良达老法师。
不久离闽省,南游广东曹溪南华寺;转而北上前往南海普陀山礼拜大悲观世音菩萨;是后往宁波阿育王寺礼拜佛陀舍利。转而行脚太白山天童寺谒太白山义兴老和尚塔,礼拜八指头陀塔。 是时适逢天童寺开戒,圆瑛老法师为戒和尚,上人往受俱足戒,圆瑛老法师早年曾游台,已先知上人声誉,故受圆老甚器重。
圆老深知台湾寺院风俗,知道一般台湾僧人很少吃苦,深恐上人不能克戒期中之困难,乃婉劝上人说:「恐怕不堪受苦,可暂住上客堂,仅在必要时入戒堂受训……」上人深感圆老慈爱,但愿与一般僧众同入戒堂,不畏肤体之折磨,愿学大陆庄严僧行。圆老深为之嘉许赞叹。 民国廿三年春天受戒毕,明朗风光给与一行脚僧人者,非春之妩媚与良辰美景,而是明心见性,得无挂无碍的快乐。年轻的和尚这时正如春天里的万物发挥着青春的生命力,但所追求的是无上的佛法,证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上人曾自吟一诗:
未偿夙愿落红尘,游戏浮生廿四春,
往事回头如梦醒,一朝见性证吾真;
本来面目何曾失,自有衣珠岂患贫,
到处随缘无住着,为谁欢喜为谁嗔。
离开天童寺后,经镇江渡扬子江到瓜州。在扬州高旻寺上人曾拜谒来果和尚;其后游焦山、金山,到处参访高僧。未几游西湖净慈寺、灵隐寺、天竺寺及附近风景名胜。经武汉,在武昌参观世界佛学苑,转而往庐山等胜地,所游各处均咏诗留念。
二十三年七月,不辞路途远涉,步行二月前往九华山礼拜地藏菩萨圣迹。当时大陆到处均有盗匪,每遇灾难则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以镇定的心情渡过种种危难。
于九华旅途,有一次乘船渡江,舟至江中,随后即有一船加速追来,上人疑为盗船,念出家人,无可挂碍,不以为意,但奇怪的是盗船无法追及上人所乘者,上岸后,即匆匆登山,行至一休息地,乌瞰山下发现一群人在争吵,其中之一为所乘小舟之船夫。船夫说:「我故意慢行,但你们不中用……何以不赶快追来?」,那些人回答说:「站在你的船头的那个穿白衣的美人,当我们的船快靠近时,他作一手势将船推开,船又离了好远……。」船夫一再否认船上有穿白衣的美人,并说仅有一乘客而已。上人在山坡上听了这些话,始知所搭为盗船,深为惊奇,而盗贼所说的穿白衣者,岂不是白衣大士(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初,上人游奉化雪窦寺,并作「雪窦游记」一文。游记上云:「余游雪窦有三目的在焉:一为拜访太虚大师,二领略雪窦风景,三预备避暑过夏……」。
可惜,时适太虚大师外出弘法,以未得在此时参见为憾。上人「称性而游」,朗吟数诗。「游记」除了记载雪窦胜景外,末写游雪窦感想,文云:
「余以三目的游雪窦亦得三感想者:一、虚大师为佛教领袖,现代高僧,而教弘慈宗,锡卓名山;二、雪窦为浙东名胜,禅宗古刹,而得菩萨应化,高僧住持;三、弥勒为当来下生,一生补处,托名山以显瑞,得高僧而传道:夫岂偶然哉!可称天造地设。而余得游兹山非三生有幸乎?盖山有高僧圣迹其名益着,僧住名山弘圣教,其德益彰,菩萨迹应名山,法付高僧,其圣普被,宁易得哉!……。」 是时宝静法师当观宗寺主讲,上人前往参学。时因贫穷无力购买参考资料,乃利用夜间同学已休息时,借其参考书而读之。但学院规矩,作息有一定的时间,有时不得不避开督学的巡视。上人极专心,进度甚速。
一日宝法师出一问题,曰:「弥杀弥慈」,系取材自指曼外道央掘摩罗的故事。试问其道理何在?令诸学生申论之。诸学生均不得要领,无从下笔。上人曾著论文,论其道理,同参将该文发表于「宏法月刊」,但没署上人法号。宝法师读该论文,惊叹著者学力,见地高超,深为赞美,后来宝老知为上人所作,嘉许赞美备至,且决定聘请上人任副讲法师。
上人知道宝法师决定请他任副讲,至为惊讶,于是乘夜整装,黎明逃出观宗寺,事为宝老所发现,即令使者前往追回,使者追了六、七里,力陈宝老聘请至意,上人则托使者,转呈宝老说:「不远千里前来大陆,目的在于求学,绝无意讲授。老法师慈意至为感激,但无论如何,不能应命。」于是赶程入天台山。 上人在台之时,已略研究天台教观,但到国内以后,并不固执一定要在天台求法,因此到处漫游参学礼拜,但因缘造成,上人终于实践最初的愿望。
是时静权老法师在天台主持学院,上人拜谒静老,甚得器重。天台佛学院规章分课程为初学与专修两部,凡入专修部必先修初学课程,上人因佛法精通,学力甚佳,所以即入专修部研究,在此期间研究四教仪、法华及天台教观。在天台求学方法有如在观宗寺时,不分昼夜专心攻究,且夜间利用佛前海灯读经,三年之内大藏经中的重要部分,几乎全部熟读。后来并曾在天台任副讲法师。 上人离台内渡之初,曾「拟作十年游」,计划在国内作较长期的住锡。不幸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发生,继之八一三,中日关系继续恶化。时台湾为日所据,上人既为台籍人士自不免被歧视。有时甚至被误会为:「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又深恐被当局注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怀疑,因此不得不离开天台,时为民国二十八年,上人二十九岁。
那时全面抗战已开始,到处烽火,一时无法到上海,路经梅溪,适遇澹云法师于梅溪观日山房。澹法师与上人系在天台时的同参执事,因此深得澹师的欢迎并留暂住观日山房。
是时澹法师在梅溪设一学院。上人应邀讲楞严经。上人说法的方法极佳,深入浅出,听者易于了解,甚得学生欢迎。听讲的诸弟子信士中,有位郭胜中居士,赞美说:「上人的辩才,为前所未闻」,不胜佩服,居士特别拜谒上人,说彼住在上海,如有机缘莅临上海,请一定到其寓一游。
在梅溪过一短时期,经澹法师得一军部首长的帮助,得军部出一张身份证明书,并特派卫兵保护上人,终于到达上海,之后,郭胜中居士探知上人挂锡曹洞宗上海别院,特请上人到功德林欢宴供养,又赠归台的船费。上人由于不了解当时上海的风气,将郭居士结缘以及所有一切积蓄,竟在电车内被扒手盗光,一时无法返台。
后来受台籍僧人荣宗法师的帮忙与交涉,得日本领事馆准许上人搭乘军用的运输船返台。不意到了将出发时却又临时拒绝上人登船,但此船离沪不久,竟触水雷而被炸沉没。这一无理的拒绝,究竟是幸运的巧遇,或佛陀菩萨有意留上人为大乘佛教弘法?
又过了一星期,上人乘商船安全地回到基隆。 这时凡留学或游览祖国的台民,均被日本政府当局疑为「危险份子」,甚至被认为可能是带有特殊任务的间谍,许多在这时回来的人,只因「可疑」而被拷问,甚至不堪苦刑以致丧命。
上人还没到达基港,则已被船上的便衣人员跟踪,水上的特务人员时常监视上人的行动。船航行了二日就被盘问:为什么前往中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中国遇到了那些人?找那些人做些什么?有那几个朋友在中国?为什么在这时候回来?等等,
到了基隆又被一个不同的人所侦询,但所答的与第一次盘问时完全相同,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所答的年、月、日、地点、人物、因缘、过程等等也完全一致。日本政府当局,并不因此而放心,第二天又问其一、二,但没有一句走差。当时回台的人,往往只因在反复侦询中有一、二句前后不一致,被认为「可疑」而受虐待或苦刑。但上人的道范庄严,使日人畏而敬之,虽说是被软禁,但享受着高等待遇。除了三餐外,报纸、茶点,按时奉送,且独住一清净的房间。
上人巍巍不动安然的态度,行住坐卧不离佛法的规制与闭在关房样,无可烦恼,无所挂碍,也没有痛苦。认为闭关有时还要食住的烦恼,现在不必挂虑这些,且警察为侍者,安全地守护着。每日可以安心地念佛、持咒、打坐,生活十分安定,对于个人全无挂碍只是有时起了大悲想:何时才能有机会实践弘法的誓愿与任务□
在这时期,又有几个不同的「侦探」人员前来「闲谈」,所谈的不外乎大陆游历经过。这种侦询的报告,一层一层地送到最高机构的森特务长(日人)的地方。森氏读了那些报告深受感动,并特访上人说:「根据他们多次的报告,我知道您的人格。我曾经将多次的报告一一核对,没有一句差错,人们有时就是所说的全为事实,但多次的答案往往会忽略其一、二,或答错了一两句话。我从这些报告了解您,不但是个学问道德修养极优,人格高尚的高僧,且可以证实您的定力功夫,我愿作证您所说的全是事实,确是仅是一个佛教传教师,绝非不法份子。」虽然森氏如此尊敬上人,由于任务并没有即刻得到释放。
不久有一天下午三时,当上人正在持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忽然有个穿西装的青年来访,青年一见上人就问「和尚,您岂不是斌宗法师?」上人说:「是的,但居士怎知道我的名字?」「喔□您忘了。以前见过您的。」「居士,您的尊名是……」。那青年笑着说:「喔!偶然的机会,以后再谈吧!我住在观音山,您稍等一会儿,本圆和尚会来保释您出去的。」说完这句话那青年就走了。
次日果然本圆和尚与日僧田洼前来保释,森氏知道这事,特在上人离开关房之前赶来说:「师父,我相信您,尊敬您,但以后不论您回到台中或别的地方,恐怕免不了再有别人找麻烦,这是我的名片,特别证明您的人格,相信当有人怀疑您的时候,它会发生效力的。」由于感动敬仰,森氏特别赠送私人证明文件,让上人得安心地布教。
事后上人前往圆山向临济宗布教总监高林玄宝老和尚(日僧)道谢。当时高林玄宝和尚对于日本在台湾的政府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当他派田洼前往基隆作证时,上人立刻得到自由。是时,适逢一青年于临济寺。那青年瞻仰法相:「威仪风度,庄严备至,令人一见而知为高僧大德」;知:「斌公戒行庄严,品德兼优,为当世佛教之大善知识」,倾心仰慕,恳请上人披剃为僧,归依为上人弟子,赐号印心。
之后上人往观音山向本圆老和尚礼谢,问起老和尚怎会知道他被禁海关时,老和尚说:「是日下午三时左右,有一青年前来观音山对我说:“斌宗法师从大陆回来被禁海关,希望您前往保释。”当时我对那陌生人的话信疑参半,后来想,这句话不会是假的,也就深信不疑,下山拜访高林老和尚,他也即刻答应,派田洼同我到基隆。」问起那青年的名字、住址,本圆老和尚也说不知道,而老和尚见到那青年的时刻与那青年访上人的时候几乎同时,两人均感奇异。以当时的交通情形计算,下午三时多离开基隆,黄昏之前是否能到达观音山尚属疑问,何况同时?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为了向那青年道谢,上人特在观音山、台北、基隆之间找寻半个月,但始终没得到那青年的信息。为此,上人并再到基隆访守关的警察,也不得而知,警察甚至说:「因一时糊涂,那青年从那一门进来都没注意到。」守关警察也看见那青年的访问,但却忘记干涉他进入关内。在大陆多次遇难也常常得到不知姓名的人帮助,而以此次最感不可思议。闻者均认为这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感应。
归台后不久,即南下龙湖庵讲地藏经,是上人归台后第一次弘法。此次法会盛况空前,首开台湾僧人研究经典的风气,让台湾的佛教徒得了解「出家」「佛陀」「菩萨」等等意义,转变「应酬佛事」为「研究圣法」。 二十九年三月,上人东渡日本,访游日本各大本山,比较研究中、日佛教的不同。所到各处均受日人热烈欢迎。在这期间上人有次在日本歧阜县美浓清泰寺住锡,遇一台籍青年,那青年不胜钦佩仰慕上人庄严大德,同年七月随之归台,是后归依为上人弟子,得上人赐号觉心。
此后印心、觉心二师未尝远离上人左右,追随上人到处说法。 民国二十九年秋,上人应请,讲阿弥陀经于南部佛教胜地——大岗山超峰寺、龙湖庵。九月讲大乘金刚经于屏东东山寺,并应潮州等处寺院及各机关团体之请,或通俗演讲,或随缘开示。是时虽台湾为日人所据,且正积极推行「皇民化」,学校、机关团体均禁用台语,但上人到处演讲从不曾用日语。每次演讲均有不少信士归依佛教。
三十年二月,上人应大溪福份山斋明禅寺之请,讲般若心经,在法会第三天,经题「般若」二字刚为讲毕,正要继续讲解「波罗密多」四字时,该寺住持孝宗师偕曾秋涛居士等,向上人要求说:「台湾向乏讲经机会,佛法罕闻,教义茫然,今赖师以开风味,此未曾有之法会,在座大众虽皆踊跃倾听,惜未尽明了,弗获全益,若如风过耳,不免有负法师一片苦口婆心呢!我们虽曾事笔记,然皆记一漏十,不成全璧,敢恳法师不惜辛苦,牖诲后学为怀,每日编成讲义油印分给听众,俾目□耳闻易于领悟则得益较多,不知法师以为如何?」是故在这次弘法期间上人着成「心经要释」一书。
同年再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于台北净土宗布教所,冬讲无量寿经于北投法雨寺。
三十一年秋七月讲金刚经于台中宝觉寺,又在雾峰灵山寺讲阿弥陀经,再讲金刚经于新竹净业院。当上人在灵山寺说法时,六、七十年未曾开花之牡丹竟告开花,林献堂老居士认此为奇迹,作诗赞叹上人。
是年冬,上人因讲法过劳,心脏衰弱,遂受请静养于新竹法王寺,但亦时常为诸弟子开示用功法要,及修学方法。 这时新竹的信徒都深望上人在新竹建寺为弘法道场,在法王寺挂锡期间,路经古奇峰,观其风景佳丽,且可眺望临海,赞叹不已!
古奇峰为新竹八景之一,因此地主陈新丁先生表示千万金也不愿放弃该地。但是不久,陈氏夜梦其亡母,对他说:“新丁,我处境很苦,希望有大德高僧救拔我,听说新竹的善信们不是欲请有一高僧拟在此山建寺,你当答应他”等等。陈氏深引为奇异,于是特拜见上人,欢迎在古奇峰建寺。
那时的台湾佛教徒们对佛教的认识不够,且佛寺林立,时有不肖之徒,借建寺为名到处欺骗,因之出家人常被轻视,所以上人是时只接受几位归依弟子的发心,有:郑根木、郑纯、唐妹珠(即现在之道心比丘尼)、苏明志(明心尼师)、郑林剑华(雪心)诸居士等人发起,热诚拥护,法源寺遂略成规模。
建筑期间,位置方向,形式蓝图均为上人所指示,由于经济所限,印心、觉心二师及唐、苏二居士且兼工役,劳苦至甚。
三十三年法源寺落成,净业院住持永修、永善二位尼师,奉赠前自大陆南海普陀山迎回之西方三圣像,二师与其弟子均亲自奉上佛像至法源寺。
在这年间,如逢佛陀圣诞,或菩萨圣诞,上人则说法为诸弟子信士等开示,闻者皆大欢喜。 三十三年秋,战局紧张,盟机轰炸台湾,日政府命令疏散,上人同觉心、印心二师避于金刚寺。上人极慈悲,很关心未疏散弟子信徒的安全,因此,三十四年春,笔者特离家慈(雪心),避难于金刚寺,蒙上人之恩极大。不久唐居士等亦至金刚寺,上人或时为诸弟子开示。上人法相威严,不但为诸弟子所敬仰,且为狮山所有人士所畏敬。
八月,战事结束,一日上人回法源,狮山居民知之,拥乘夜劫金刚寺。但不知是何因缘,上人却在当日回山。深夜,大汉六、七人,带火把绳索到寺。此时寺内仅有上人,印师、笔者(十二岁)三人,上人在楼上发声止之;为诸浪汉开示,彼等因敬畏上人威德,自动散离。
九月离狮山还回法源寺,十一月讲弥陀经于中坜元化院。 三十五年,上人感于过去的台湾佛教,深受日人的遗毒,欲须显明祖国佛教的正统,非力弘不可,故特创设佛学高级研究班,除在法源说法外,上人较少往来南北讲经,三十六年春,则在新竹佛教支会讲地藏经,此时盛况空前,听讲诸弟子信士来自南北,几全台各处均有之。此时听众大部分住在新竹,每晨、每晚由大弟子轮流复讲。冬十月再讲地藏经于狮山元光寺。十二月在台中宝善寺讲普门品。三十七年夏在狮山劝化堂讲弥陀经。八月应新竹魏经龙、周敏益诸居士之请,在本愿寺讲楞严经,本拟讲期为三年,但因经济情形不能安定,无法支持太久,月余而散。
上人说理精辟,能深入浅出,凡遇深奥难明处,每设喻以晓之,务使听众悉能明了而后已!苦口婆心,谆谆善诱,令人赞叹不已。
上人每次讲经,均依天台五重玄义讲释。对每一语句则又「预释」、「分释」、再「合释」。因此有一不识字的老人竟在听完一部经典后,能通国文。
三十七、八年间,上人也曾在新竹公共场所作较通俗式的演讲,但所讲有时仍是一部经典,法会期间或一星期,或十天。
三十八年冬,上人为要专门造就弘法人材,在法源寺创办南天台佛学研究院。 从大陆归台后,上人不辞劳苦,为诸弟子信徒说法。自三十八年政府迁台,大陆诸法师大德随政府来台,上人至感安慰,认为宝岛佛教的黄金时代来临,不但传教不致中断,且将是佛教开始复兴之时,上人并特关照诸台籍弟子信徒,勿因语言不便,而失去闻法的好机会,应多多听闻大陆诸法师说法。既喜慰弘法有人故自三十九年来很少出门,四十年佛陀成道日开始正式闭关专为诸学子们讲学。 四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放关,十二月十一日即在新竹中山堂演讲。十二月十三日应台北诸信徒之请,在台北蓬莱国校礼堂讲阿弥陀经,听众空前,皈依者极多。
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又南下屏东东山寺讲楞严经。虽是春天,南部气候炎热,上人血压甚高,诸弟子信徒均为上人而祈祷。楞严法会之后,上人往冈山说法,并在南部到处演讲开示,直到三月中旬才回寺。
同年四月,台中莲社传授在家菩萨戒,上人南下主持。
此外,上人也曾往桃园麻疯院(乐生院),为一病群患者说法,多数患者皆皈依上人。
同年十一月一日,为觉心法师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创设南天台弘法院。
四十五年春,为印心法师创建法济寺于碧潭山上,其间上人或居法源,或住锡碧潭,或莅弘法院,巡视指导。
果满示寂
四十六年八月,上人健康情形一日不如一日,因之就医于郭内科,住锡弘法院静养。
九月二十五日在弘法院,长寿会席上为诸弟子信徒们开示,此为上人最后的一次说法。之后健康情形未见好转,十一月,上人已宣示欲入涅槃,经诸弟子苦留长期住世,始允入院就医,印心、广心二师随侍左右,日夜服侍不懈,觉心师则每日数次到医院问候。上人极慈悲,仍关怀诸弟子,知弘法院寺务繁多,常对觉心师说:「觉心,你很忙,可以不必常来。」
农历二月初一,回弘法院静养,法体已渐见好转,直至十九日(国历四月七日)晨观世音菩萨圣诞节,安祥示寂于弘法院。
国历四月十三日,荼毗典礼,得舍利甚多。
上人是「解」「行」并重的高僧,一生大慈大悲,弘法利生,戒行极其庄严。诸弟子信徒们已决定在新竹古奇峰南天台法源讲寺山上建斌宗大师舍利塔,以永念上人事迹。
完 乐清 朱镜宙 撰
斌宗和尚,俗姓施,名能展,其曾祖修嵌公,自福建晋江,迁居台湾之鹿港,祖至斤,以货殖致饶。父眛目,为邑名医,母黄,有贤行。和尚生而颖异,童年能诗文,一日,有贾人以故籍致,发视之,咸内典也,自是深悟无常之理。白父欲出家,未许,竟自亡去,途次,被截回,禁之楼上,夜缒而遁,披绋师山,年方十四也。居三载,不忍与邪命存活者伍,乃结茅汴峰,藉馆榖自给。有优婆夷施米巨斛,却不受。虽箪瓢屡空,怡如也。居恒以台瀛佛法,蔑视律仪,蓄妻育子,咸名出家,慨然以扶敝起衰自任。民国二十二年萧然瓶钵,西浮宗邦,用资取则。明年春,受具戒于圆瑛和尚。秋,发足雪窦,步行礼九华,渡江遇盗船尾随,和尚默持观音圣号,盗不得近。又明年,参学观宗,宝静法师,以鸯掘罗弥杀弥慈故事试诸生,毋一能应,师独畅申其旨。宝静惊喜,欲聘为副讲,不告而去。闻当代台宗耆宿静权老和尚,主讲国清,遂往依止,尽传其学。方是时,倭寇窥边,河朔继陷,大江南北,烽火频惊,乃挥泪告归,迨舟舣基隆,日本谍务,幽之海关,更番侦鞫,答无二语,如是内外信使阻绝者逾月,和尚持观音圣号益谨,忽一青年,言来自观音山,师乃旧识,并谓本圆和尚,将来解救,语讫不见,逻者森严,亦未见其出入,无何,果如所云,时民国二十八年也。冬讲地藏经于冈山龙湖庵,是为台僧正式说法之始。
一日,偶经新竹古奇峰下,喜其地依山面海,遂有结茅终老之志。业主陈新丁,感母示梦,始献之。逾年,寺落,额曰:南天台法源寺,示不忘法乳也。旋循台北弟子请,创弘法院于行都,并就碧潭涵碧峰,诛茅数弓,聊为避嚣计焉。先是,师因弘法过劳,时感怔忡,二十年间,南北栖栖,未遑宁处,至是不支,民国四十七年二月观音成道日,卒于弘法院,春秋四十有八,僧腊三十四,荼毗获舍利百余,大者如拇指,内外莹澈,感叹希有云。和尚浓眉巨目,威仪严肃,四众见之,罔不敬畏,综其生平,南北谈经,不下三十会,壹遵天台家法,深入浅出,雅俗共喻,是以每登讲坛,座无虚席,恒及千人,虽日警厉行皇化,严禁台语,和尚勿顾,可谓难能也已,初,师既归,本圆和尚,劳之山寺,席次,基隆某大德曰:中国佛法,持戒茹素,乃是小乘,惟有日本,荤素并进,方称大乘。和尚曰:日本大本山管长,大乘抑小乘?某曰:管长当然是大乘。曰:管长持戒素食,不让中国;既是大乘,胡薄彼为?其讲弥陀经于灵山寺也,一六十年未花之牡丹,忽尔盛放。应供之日,台中某长老曰:人之有口,犹城垣之有门也,鱼虾蔬肉,既可自由出入于城之门,而谓人之口,不能荤素并进,可乎哉?和尚曰:诚如尊论,城门尚可出入粪便,将谓人之口亦如之邪?阖座闻之,轩渠不置。和尚曲高和寡,不能见容于并世类如是!其门墙严峻,殆非得已也。著有般若心经要释、阿弥陀经要讲、山居杂咏等行世。某年月日,将塔舍利于寺侧,弟子以状来请铭。铭曰:
举世醉而独醒,举世浊而独清,卓立而不阿兮,乃法门之干城,抑示寂之胡驶兮,犹长夜之失明灯,閟尔宫兮妥尔灵,其乘愿重来兮,普度夫有情。
本文是根据遗作,及笔者所知,简要地叙述而已。 上人俗姓施,名能展,民国前一年(辛亥)二月初五,降生于台湾鹿港。其先世祖父为当地巨富,父昧目公为当代名医,文学德行亦称于世,上人少时智慧超人,五岁时就有成人的智慧,能教化同阵的小朋友行善,诸恶莫作。天资超人,坐立端正,品性良好,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六、七岁时,已通粗浅文字,喜读经书,吟诗。
年十二,始正式受教于私塾,但教师所教有限,深感不足。是时书塾对于学生系个别教授,因此购买许多不同类的书籍,当教师给同学讲解其他课程时,则虚心旁听,所读科目甚多,文、史、诗、词、均有之。上人极用功,读书不分昼夜,往往因之过度疲倦,有时甚至体力不支而伏在桌上假睡。如是一年,所学多常人数倍,且较诸正式授课的同学精通,常为同学师。
是时有一年较长的同学学诗,上人也旁听,约学半年,一日,同学求其师题诗扇上,师以事尚未顾及,上人乃作:“绿柳萋萋淡月幽,清江曲曲抗汀洲,平沙一片万余里,静夜无人水自流”一诗,以和扇上秋月美人乘凉柳树下佳景。教师惊其神慧天才,嘉奖赞美至极,此后倍加热心指导,上人学问更是一日千里。 十四岁那年春天,一日,遇一买卖古书者挑担许多书籍从门前经过。上人素极爱好古书,乃唤住该书贩,观其书籍,多为前所未闻未见者。原是一佛寺废去,经典佛书被拍卖,书贩所卖者多为佛教经典,上人以好奇而购之。从那经典得感悟世间无常,深感「功名富贵浑如梦」(上人十四岁时作七言诗中之一句),乃发出家学佛,救度众生之宏愿。又念割台事及其后经过,更证实世界上的「无常变幻」。
上人由是曾要求出家,但未得其父之许可。这时追求真理之心愿已坚决,于是有一天上人逃走到法云寺,家人因念年纪尚小,不甘其受出家生活之「苦」到处寻找,终被追回。
回家后,被禁于楼上,但日常生活已宛如出家人,维持素食,谨守戒行。日读经书,禅坐,对佛学更加了解,出家心志弥更坚决。又因当时一片清净童心,无烦无碍,学禅甚易,往往一坐数日,朗然虚空境界。
四月初七夜,上人用绳索穿过屋梁,将其一端系于一件笨重的家俱,引其另一端,乘家人已入睡的时机,安全地从楼上坠下,逃往狮头山礼闲云禅师出家。其后也曾漫游全省较有名的佛教胜地,如大湖、观音山、五指山、冈山等处。 十七岁的那年,因种种因缘,上人决定结茅独居于汴峰(台中市郊头汴坑)。每日授课学生以维持自给的生活,不愿受友人或信士的供养,也不接受馈赠。有时柴米皆尽,乃先向学生借用,及束修时照数退还。那时有一信士金山夫人(即后来狮头山海会庵第一代住持比丘尼达明师),曾以大量米粮供养,上人不受而退还之。
山居物资生活,往往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要求,但上人却过着乐道的生活。任何语辞难以说明此时的情况,但如以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比当年上人的汴峰生活,则是最恰当不过的。
结茅汴峰计六年(十七岁到廿三岁),此时授课外,尚自己用功研究法华、楞严诸大乘经典,后来也曾授信徒以大乘教义。
当时,与上人往来诸友,大都为文学界学者,有王了庵、陈仲衡、王德修、施梅樵等诸士。除了自修讲学外时常应诸士之邀,谈诗,或击钵联吟。在台中文学界诗会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人;席上如无上人在,则盛况失色,所以诸士常说:「如不往头汴坑抬下时钟(诗僧,台语与「时钟」音相似),则不知时(诗),事不能为也」。遗著「烟霞吟稿」则此时所作。 当时台湾佛教,几乎仅限于「做佛事」,僧尼对于经典大都不求了解,甚至不知「行」为何物。当时所谓「说法」不过是世俗因果报应之类,或佛教故事而已。三藏经典只见陈列,而不为四众所知解。僧尼虽诵佛经,但大多数仅是盲念,并不解佛法真实义。至于信仰更是混乱,完全不知正信与迷信之分。佛教徒甚至礼拜神鬼、外道,或与神道邪教合流。
上人悲叹海角孤岛的台湾,不得大法师指导,乃发心前往祖国留学,求法。同时渴望礼拜名山古刹、菩萨圣迹,参访高僧大德。
民国廿二年春,决心内渡,虽是贫僧,但贫穷无法阻止向上心愿。上人不愿化缘或求助于友人,甚至不受诸友送行,悄然离开茅房,但留一诗以别骚坛诸诗友。离开汴峰时,仅有一知己信徒发觉,乃赠十元为旅途之用,这对于一贫僧而言,却是一大笔的数目。
离开基隆港到厦门,从此开始参拜名山圣迹。 初渡大陆后,上人在福建游学,先游鼓山涌泉寺,在此期间曾参访虚云老和尚,且曾与虚公老和尚暨宗镜心月二师同登屴崱峰。上人早有参访古月和尚之念,但不幸来时师已西归,乃吟诗念之。此外,曾与会泉法师等同游鼓浪屿,亦曾谒良达老法师。
不久离闽省,南游广东曹溪南华寺;转而北上前往南海普陀山礼拜大悲观世音菩萨;是后往宁波阿育王寺礼拜佛陀舍利。转而行脚太白山天童寺谒太白山义兴老和尚塔,礼拜八指头陀塔。 是时适逢天童寺开戒,圆瑛老法师为戒和尚,上人往受俱足戒,圆瑛老法师早年曾游台,已先知上人声誉,故受圆老甚器重。
圆老深知台湾寺院风俗,知道一般台湾僧人很少吃苦,深恐上人不能克戒期中之困难,乃婉劝上人说:「恐怕不堪受苦,可暂住上客堂,仅在必要时入戒堂受训……」上人深感圆老慈爱,但愿与一般僧众同入戒堂,不畏肤体之折磨,愿学大陆庄严僧行。圆老深为之嘉许赞叹。 民国廿三年春天受戒毕,明朗风光给与一行脚僧人者,非春之妩媚与良辰美景,而是明心见性,得无挂无碍的快乐。年轻的和尚这时正如春天里的万物发挥着青春的生命力,但所追求的是无上的佛法,证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上人曾自吟一诗:
未偿夙愿落红尘,游戏浮生廿四春,
往事回头如梦醒,一朝见性证吾真;
本来面目何曾失,自有衣珠岂患贫,
到处随缘无住着,为谁欢喜为谁嗔。
离开天童寺后,经镇江渡扬子江到瓜州。在扬州高旻寺上人曾拜谒来果和尚;其后游焦山、金山,到处参访高僧。未几游西湖净慈寺、灵隐寺、天竺寺及附近风景名胜。经武汉,在武昌参观世界佛学苑,转而往庐山等胜地,所游各处均咏诗留念。
二十三年七月,不辞路途远涉,步行二月前往九华山礼拜地藏菩萨圣迹。当时大陆到处均有盗匪,每遇灾难则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以镇定的心情渡过种种危难。
于九华旅途,有一次乘船渡江,舟至江中,随后即有一船加速追来,上人疑为盗船,念出家人,无可挂碍,不以为意,但奇怪的是盗船无法追及上人所乘者,上岸后,即匆匆登山,行至一休息地,乌瞰山下发现一群人在争吵,其中之一为所乘小舟之船夫。船夫说:「我故意慢行,但你们不中用……何以不赶快追来?」,那些人回答说:「站在你的船头的那个穿白衣的美人,当我们的船快靠近时,他作一手势将船推开,船又离了好远……。」船夫一再否认船上有穿白衣的美人,并说仅有一乘客而已。上人在山坡上听了这些话,始知所搭为盗船,深为惊奇,而盗贼所说的穿白衣者,岂不是白衣大士(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初,上人游奉化雪窦寺,并作「雪窦游记」一文。游记上云:「余游雪窦有三目的在焉:一为拜访太虚大师,二领略雪窦风景,三预备避暑过夏……」。
可惜,时适太虚大师外出弘法,以未得在此时参见为憾。上人「称性而游」,朗吟数诗。「游记」除了记载雪窦胜景外,末写游雪窦感想,文云:
「余以三目的游雪窦亦得三感想者:一、虚大师为佛教领袖,现代高僧,而教弘慈宗,锡卓名山;二、雪窦为浙东名胜,禅宗古刹,而得菩萨应化,高僧住持;三、弥勒为当来下生,一生补处,托名山以显瑞,得高僧而传道:夫岂偶然哉!可称天造地设。而余得游兹山非三生有幸乎?盖山有高僧圣迹其名益着,僧住名山弘圣教,其德益彰,菩萨迹应名山,法付高僧,其圣普被,宁易得哉!……。」 是时宝静法师当观宗寺主讲,上人前往参学。时因贫穷无力购买参考资料,乃利用夜间同学已休息时,借其参考书而读之。但学院规矩,作息有一定的时间,有时不得不避开督学的巡视。上人极专心,进度甚速。
一日宝法师出一问题,曰:「弥杀弥慈」,系取材自指曼外道央掘摩罗的故事。试问其道理何在?令诸学生申论之。诸学生均不得要领,无从下笔。上人曾著论文,论其道理,同参将该文发表于「宏法月刊」,但没署上人法号。宝法师读该论文,惊叹著者学力,见地高超,深为赞美,后来宝老知为上人所作,嘉许赞美备至,且决定聘请上人任副讲法师。
上人知道宝法师决定请他任副讲,至为惊讶,于是乘夜整装,黎明逃出观宗寺,事为宝老所发现,即令使者前往追回,使者追了六、七里,力陈宝老聘请至意,上人则托使者,转呈宝老说:「不远千里前来大陆,目的在于求学,绝无意讲授。老法师慈意至为感激,但无论如何,不能应命。」于是赶程入天台山。 上人在台之时,已略研究天台教观,但到国内以后,并不固执一定要在天台求法,因此到处漫游参学礼拜,但因缘造成,上人终于实践最初的愿望。
是时静权老法师在天台主持学院,上人拜谒静老,甚得器重。天台佛学院规章分课程为初学与专修两部,凡入专修部必先修初学课程,上人因佛法精通,学力甚佳,所以即入专修部研究,在此期间研究四教仪、法华及天台教观。在天台求学方法有如在观宗寺时,不分昼夜专心攻究,且夜间利用佛前海灯读经,三年之内大藏经中的重要部分,几乎全部熟读。后来并曾在天台任副讲法师。 上人离台内渡之初,曾「拟作十年游」,计划在国内作较长期的住锡。不幸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发生,继之八一三,中日关系继续恶化。时台湾为日所据,上人既为台籍人士自不免被歧视。有时甚至被误会为:「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又深恐被当局注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怀疑,因此不得不离开天台,时为民国二十八年,上人二十九岁。
那时全面抗战已开始,到处烽火,一时无法到上海,路经梅溪,适遇澹云法师于梅溪观日山房。澹法师与上人系在天台时的同参执事,因此深得澹师的欢迎并留暂住观日山房。
是时澹法师在梅溪设一学院。上人应邀讲楞严经。上人说法的方法极佳,深入浅出,听者易于了解,甚得学生欢迎。听讲的诸弟子信士中,有位郭胜中居士,赞美说:「上人的辩才,为前所未闻」,不胜佩服,居士特别拜谒上人,说彼住在上海,如有机缘莅临上海,请一定到其寓一游。
在梅溪过一短时期,经澹法师得一军部首长的帮助,得军部出一张身份证明书,并特派卫兵保护上人,终于到达上海,之后,郭胜中居士探知上人挂锡曹洞宗上海别院,特请上人到功德林欢宴供养,又赠归台的船费。上人由于不了解当时上海的风气,将郭居士结缘以及所有一切积蓄,竟在电车内被扒手盗光,一时无法返台。
后来受台籍僧人荣宗法师的帮忙与交涉,得日本领事馆准许上人搭乘军用的运输船返台。不意到了将出发时却又临时拒绝上人登船,但此船离沪不久,竟触水雷而被炸沉没。这一无理的拒绝,究竟是幸运的巧遇,或佛陀菩萨有意留上人为大乘佛教弘法?
又过了一星期,上人乘商船安全地回到基隆。 这时凡留学或游览祖国的台民,均被日本政府当局疑为「危险份子」,甚至被认为可能是带有特殊任务的间谍,许多在这时回来的人,只因「可疑」而被拷问,甚至不堪苦刑以致丧命。
上人还没到达基港,则已被船上的便衣人员跟踪,水上的特务人员时常监视上人的行动。船航行了二日就被盘问:为什么前往中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中国遇到了那些人?找那些人做些什么?有那几个朋友在中国?为什么在这时候回来?等等,

到了基隆又被一个不同的人所侦询,但所答的与第一次盘问时完全相同,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所答的年、月、日、地点、人物、因缘、过程等等也完全一致。日本政府当局,并不因此而放心,第二天又问其一、二,但没有一句走差。当时回台的人,往往只因在反复侦询中有一、二句前后不一致,被认为「可疑」而受虐待或苦刑。但上人的道范庄严,使日人畏而敬之,虽说是被软禁,但享受着高等待遇。除了三餐外,报纸、茶点,按时奉送,且独住一清净的房间。
上人巍巍不动安然的态度,行住坐卧不离佛法的规制与闭在关房样,无可烦恼,无所挂碍,也没有痛苦。认为闭关有时还要食住的烦恼,现在不必挂虑这些,且警察为侍者,安全地守护着。每日可以安心地念佛、持咒、打坐,生活十分安定,对于个人全无挂碍只是有时起了大悲想:何时才能有机会实践弘法的誓愿与任务□
在这时期,又有几个不同的「侦探」人员前来「闲谈」,所谈的不外乎大陆游历经过。这种侦询的报告,一层一层地送到最高机构的森特务长(日人)的地方。森氏读了那些报告深受感动,并特访上人说:「根据他们多次的报告,我知道您的人格。我曾经将多次的报告一一核对,没有一句差错,人们有时就是所说的全为事实,但多次的答案往往会忽略其一、二,或答错了一两句话。我从这些报告了解您,不但是个学问道德修养极优,人格高尚的高僧,且可以证实您的定力功夫,我愿作证您所说的全是事实,确是仅是一个佛教传教师,绝非不法份子。」虽然森氏如此尊敬上人,由于任务并没有即刻得到释放。
不久有一天下午三时,当上人正在持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忽然有个穿西装的青年来访,青年一见上人就问「和尚,您岂不是斌宗法师?」上人说:「是的,但居士怎知道我的名字?」「喔□您忘了。以前见过您的。」「居士,您的尊名是……」。那青年笑着说:「喔!偶然的机会,以后再谈吧!我住在观音山,您稍等一会儿,本圆和尚会来保释您出去的。」说完这句话那青年就走了。
次日果然本圆和尚与日僧田洼前来保释,森氏知道这事,特在上人离开关房之前赶来说:「师父,我相信您,尊敬您,但以后不论您回到台中或别的地方,恐怕免不了再有别人找麻烦,这是我的名片,特别证明您的人格,相信当有人怀疑您的时候,它会发生效力的。」由于感动敬仰,森氏特别赠送私人证明文件,让上人得安心地布教。
事后上人前往圆山向临济宗布教总监高林玄宝老和尚(日僧)道谢。当时高林玄宝和尚对于日本在台湾的政府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当他派田洼前往基隆作证时,上人立刻得到自由。是时,适逢一青年于临济寺。那青年瞻仰法相:「威仪风度,庄严备至,令人一见而知为高僧大德」;知:「斌公戒行庄严,品德兼优,为当世佛教之大善知识」,倾心仰慕,恳请上人披剃为僧,归依为上人弟子,赐号印心。
之后上人往观音山向本圆老和尚礼谢,问起老和尚怎会知道他被禁海关时,老和尚说:「是日下午三时左右,有一青年前来观音山对我说:“斌宗法师从大陆回来被禁海关,希望您前往保释。”当时我对那陌生人的话信疑参半,后来想,这句话不会是假的,也就深信不疑,下山拜访高林老和尚,他也即刻答应,派田洼同我到基隆。」问起那青年的名字、住址,本圆老和尚也说不知道,而老和尚见到那青年的时刻与那青年访上人的时候几乎同时,两人均感奇异。以当时的交通情形计算,下午三时多离开基隆,黄昏之前是否能到达观音山尚属疑问,何况同时?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为了向那青年道谢,上人特在观音山、台北、基隆之间找寻半个月,但始终没得到那青年的信息。为此,上人并再到基隆访守关的警察,也不得而知,警察甚至说:「因一时糊涂,那青年从那一门进来都没注意到。」守关警察也看见那青年的访问,但却忘记干涉他进入关内。在大陆多次遇难也常常得到不知姓名的人帮助,而以此次最感不可思议。闻者均认为这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感应。
归台后不久,即南下龙湖庵讲地藏经,是上人归台后第一次弘法。此次法会盛况空前,首开台湾僧人研究经典的风气,让台湾的佛教徒得了解「出家」「佛陀」「菩萨」等等意义,转变「应酬佛事」为「研究圣法」。 二十九年三月,上人东渡日本,访游日本各大本山,比较研究中、日佛教的不同。所到各处均受日人热烈欢迎。在这期间上人有次在日本歧阜县美浓清泰寺住锡,遇一台籍青年,那青年不胜钦佩仰慕上人庄严大德,同年七月随之归台,是后归依为上人弟子,得上人赐号觉心。
此后印心、觉心二师未尝远离上人左右,追随上人到处说法。 民国二十九年秋,上人应请,讲阿弥陀经于南部佛教胜地——大岗山超峰寺、龙湖庵。九月讲大乘金刚经于屏东东山寺,并应潮州等处寺院及各机关团体之请,或通俗演讲,或随缘开示。是时虽台湾为日人所据,且正积极推行「皇民化」,学校、机关团体均禁用台语,但上人到处演讲从不曾用日语。每次演讲均有不少信士归依佛教。
三十年二月,上人应大溪福份山斋明禅寺之请,讲般若心经,在法会第三天,经题「般若」二字刚为讲毕,正要继续讲解「波罗密多」四字时,该寺住持孝宗师偕曾秋涛居士等,向上人要求说:「台湾向乏讲经机会,佛法罕闻,教义茫然,今赖师以开风味,此未曾有之法会,在座大众虽皆踊跃倾听,惜未尽明了,弗获全益,若如风过耳,不免有负法师一片苦口婆心呢!我们虽曾事笔记,然皆记一漏十,不成全璧,敢恳法师不惜辛苦,牖诲后学为怀,每日编成讲义油印分给听众,俾目□耳闻易于领悟则得益较多,不知法师以为如何?」是故在这次弘法期间上人着成「心经要释」一书。
同年再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于台北净土宗布教所,冬讲无量寿经于北投法雨寺。
三十一年秋七月讲金刚经于台中宝觉寺,又在雾峰灵山寺讲阿弥陀经,再讲金刚经于新竹净业院。当上人在灵山寺说法时,六、七十年未曾开花之牡丹竟告开花,林献堂老居士认此为奇迹,作诗赞叹上人。
是年冬,上人因讲法过劳,心脏衰弱,遂受请静养于新竹法王寺,但亦时常为诸弟子开示用功法要,及修学方法。 这时新竹的信徒都深望上人在新竹建寺为弘法道场,在法王寺挂锡期间,路经古奇峰,观其风景佳丽,且可眺望临海,赞叹不已!
古奇峰为新竹八景之一,因此地主陈新丁先生表示千万金也不愿放弃该地。但是不久,陈氏夜梦其亡母,对他说:“新丁,我处境很苦,希望有大德高僧救拔我,听说新竹的善信们不是欲请有一高僧拟在此山建寺,你当答应他”等等。陈氏深引为奇异,于是特拜见上人,欢迎在古奇峰建寺。
那时的台湾佛教徒们对佛教的认识不够,且佛寺林立,时有不肖之徒,借建寺为名到处欺骗,因之出家人常被轻视,所以上人是时只接受几位归依弟子的发心,有:郑根木、郑纯、唐妹珠(即现在之道心比丘尼)、苏明志(明心尼师)、郑林剑华(雪心)诸居士等人发起,热诚拥护,法源寺遂略成规模。
建筑期间,位置方向,形式蓝图均为上人所指示,由于经济所限,印心、觉心二师及唐、苏二居士且兼工役,劳苦至甚。
三十三年法源寺落成,净业院住持永修、永善二位尼师,奉赠前自大陆南海普陀山迎回之西方三圣像,二师与其弟子均亲自奉上佛像至法源寺。
在这年间,如逢佛陀圣诞,或菩萨圣诞,上人则说法为诸弟子信士等开示,闻者皆大欢喜。 三十三年秋,战局紧张,盟机轰炸台湾,日政府命令疏散,上人同觉心、印心二师避于金刚寺。上人极慈悲,很关心未疏散弟子信徒的安全,因此,三十四年春,笔者特离家慈(雪心),避难于金刚寺,蒙上人之恩极大。不久唐居士等亦至金刚寺,上人或时为诸弟子开示。上人法相威严,不但为诸弟子所敬仰,且为狮山所有人士所畏敬。
八月,战事结束,一日上人回法源,狮山居民知之,拥乘夜劫金刚寺。但不知是何因缘,上人却在当日回山。深夜,大汉六、七人,带火把绳索到寺。此时寺内仅有上人,印师、笔者(十二岁)三人,上人在楼上发声止之;为诸浪汉开示,彼等因敬畏上人威德,自动散离。
九月离狮山还回法源寺,十一月讲弥陀经于中坜元化院。 三十五年,上人感于过去的台湾佛教,深受日人的遗毒,欲须显明祖国佛教的正统,非力弘不可,故特创设佛学高级研究班,除在法源说法外,上人较少往来南北讲经,三十六年春,则在新竹佛教支会讲地藏经,此时盛况空前,听讲诸弟子信士来自南北,几全台各处均有之。此时听众大部分住在新竹,每晨、每晚由大弟子轮流复讲。冬十月再讲地藏经于狮山元光寺。十二月在台中宝善寺讲普门品。三十七年夏在狮山劝化堂讲弥陀经。八月应新竹魏经龙、周敏益诸居士之请,在本愿寺讲楞严经,本拟讲期为三年,但因经济情形不能安定,无法支持太久,月余而散。
上人说理精辟,能深入浅出,凡遇深奥难明处,每设喻以晓之,务使听众悉能明了而后已!苦口婆心,谆谆善诱,令人赞叹不已。
上人每次讲经,均依天台五重玄义讲释。对每一语句则又「预释」、「分释」、再「合释」。因此有一不识字的老人竟在听完一部经典后,能通国文。
三十七、八年间,上人也曾在新竹公共场所作较通俗式的演讲,但所讲有时仍是一部经典,法会期间或一星期,或十天。
三十八年冬,上人为要专门造就弘法人材,在法源寺创办南天台佛学研究院。 从大陆归台后,上人不辞劳苦,为诸弟子信徒说法。自三十八年政府迁台,大陆诸法师大德随政府来台,上人至感安慰,认为宝岛佛教的黄金时代来临,不但传教不致中断,且将是佛教开始复兴之时,上人并特关照诸台籍弟子信徒,勿因语言不便,而失去闻法的好机会,应多多听闻大陆诸法师说法。既喜慰弘法有人故自三十九年来很少出门,四十年佛陀成道日开始正式闭关专为诸学子们讲学。 四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放关,十二月十一日即在新竹中山堂演讲。十二月十三日应台北诸信徒之请,在台北蓬莱国校礼堂讲阿弥陀经,听众空前,皈依者极多。
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又南下屏东东山寺讲楞严经。虽是春天,南部气候炎热,上人血压甚高,诸弟子信徒均为上人而祈祷。楞严法会之后,上人往冈山说法,并在南部到处演讲开示,直到三月中旬才回寺。
同年四月,台中莲社传授在家菩萨戒,上人南下主持。
此外,上人也曾往桃园麻疯院(乐生院),为一病群患者说法,多数患者皆皈依上人。
同年十一月一日,为觉心法师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创设南天台弘法院。
四十五年春,为印心法师创建法济寺于碧潭山上,其间上人或居法源,或住锡碧潭,或莅弘法院,巡视指导。
果满示寂
四十六年八月,上人健康情形一日不如一日,因之就医于郭内科,住锡弘法院静养。
九月二十五日在弘法院,长寿会席上为诸弟子信徒们开示,此为上人最后的一次说法。之后健康情形未见好转,十一月,上人已宣示欲入涅槃,经诸弟子苦留长期住世,始允入院就医,印心、广心二师随侍左右,日夜服侍不懈,觉心师则每日数次到医院问候。上人极慈悲,仍关怀诸弟子,知弘法院寺务繁多,常对觉心师说:「觉心,你很忙,可以不必常来。」
农历二月初一,回弘法院静养,法体已渐见好转,直至十九日(国历四月七日)晨观世音菩萨圣诞节,安祥示寂于弘法院。
国历四月十三日,荼毗典礼,得舍利甚多。
上人是「解」「行」并重的高僧,一生大慈大悲,弘法利生,戒行极其庄严。诸弟子信徒们已决定在新竹古奇峰南天台法源讲寺山上建斌宗大师舍利塔,以永念上人事迹。
完 乐清 朱镜宙 撰
斌宗和尚,俗姓施,名能展,其曾祖修嵌公,自福建晋江,迁居台湾之鹿港,祖至斤,以货殖致饶。父眛目,为邑名医,母黄,有贤行。和尚生而颖异,童年能诗文,一日,有贾人以故籍致,发视之,咸内典也,自是深悟无常之理。白父欲出家,未许,竟自亡去,途次,被截回,禁之楼上,夜缒而遁,披绋师山,年方十四也。居三载,不忍与邪命存活者伍,乃结茅汴峰,藉馆榖自给。有优婆夷施米巨斛,却不受。虽箪瓢屡空,怡如也。居恒以台瀛佛法,蔑视律仪,蓄妻育子,咸名出家,慨然以扶敝起衰自任。民国二十二年萧然瓶钵,西浮宗邦,用资取则。明年春,受具戒于圆瑛和尚。秋,发足雪窦,步行礼九华,渡江遇盗船尾随,和尚默持观音圣号,盗不得近。又明年,参学观宗,宝静法师,以鸯掘罗弥杀弥慈故事试诸生,毋一能应,师独畅申其旨。宝静惊喜,欲聘为副讲,不告而去。闻当代台宗耆宿静权老和尚,主讲国清,遂往依止,尽传其学。方是时,倭寇窥边,河朔继陷,大江南北,烽火频惊,乃挥泪告归,迨舟舣基隆,日本谍务,幽之海关,更番侦鞫,答无二语,如是内外信使阻绝者逾月,和尚持观音圣号益谨,忽一青年,言来自观音山,师乃旧识,并谓本圆和尚,将来解救,语讫不见,逻者森严,亦未见其出入,无何,果如所云,时民国二十八年也。冬讲地藏经于冈山龙湖庵,是为台僧正式说法之始。
一日,偶经新竹古奇峰下,喜其地依山面海,遂有结茅终老之志。业主陈新丁,感母示梦,始献之。逾年,寺落,额曰:南天台法源寺,示不忘法乳也。旋循台北弟子请,创弘法院于行都,并就碧潭涵碧峰,诛茅数弓,聊为避嚣计焉。先是,师因弘法过劳,时感怔忡,二十年间,南北栖栖,未遑宁处,至是不支,民国四十七年二月观音成道日,卒于弘法院,春秋四十有八,僧腊三十四,荼毗获舍利百余,大者如拇指,内外莹澈,感叹希有云。和尚浓眉巨目,威仪严肃,四众见之,罔不敬畏,综其生平,南北谈经,不下三十会,壹遵天台家法,深入浅出,雅俗共喻,是以每登讲坛,座无虚席,恒及千人,虽日警厉行皇化,严禁台语,和尚勿顾,可谓难能也已,初,师既归,本圆和尚,劳之山寺,席次,基隆某大德曰:中国佛法,持戒茹素,乃是小乘,惟有日本,荤素并进,方称大乘。和尚曰:日本大本山管长,大乘抑小乘?某曰:管长当然是大乘。曰:管长持戒素食,不让中国;既是大乘,胡薄彼为?其讲弥陀经于灵山寺也,一六十年未花之牡丹,忽尔盛放。应供之日,台中某长老曰:人之有口,犹城垣之有门也,鱼虾蔬肉,既可自由出入于城之门,而谓人之口,不能荤素并进,可乎哉?和尚曰:诚如尊论,城门尚可出入粪便,将谓人之口亦如之邪?阖座闻之,轩渠不置。和尚曲高和寡,不能见容于并世类如是!其门墙严峻,殆非得已也。著有般若心经要释、阿弥陀经要讲、山居杂咏等行世。某年月日,将塔舍利于寺侧,弟子以状来请铭。铭曰:
举世醉而独醒,举世浊而独清,卓立而不阿兮,乃法门之干城,抑示寂之胡驶兮,犹长夜之失明灯,閟尔宫兮妥尔灵,其乘愿重来兮,普度夫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