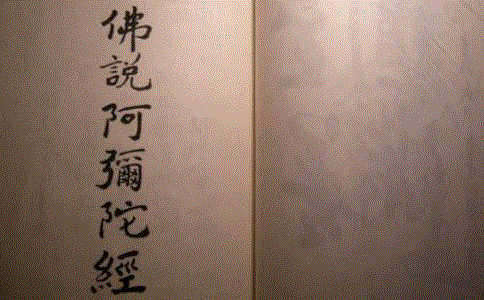四、自家宝藏 (二)“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发布时间:2024-09-03 03:40:24作者:阿弥陀经全文网
四、自家宝藏 (二)“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佛教的法,不论中观唯识。大多说理严密细致。只要不带世俗偏见,都是有路径可以通达的。禅宗以无法为法,但禅师们有上堂的开示、小参、晚参、机锋、棒喝、转语、公案、参话头等种种作略。其中许多仍然是有理路可寻,可以使人理解,如六祖的《坛经》、黄檗的《传法心要》及许多禅师的《语录》等;难解或不可理解的大多为棒喝、机锋和转语,但若经说破,也不是不可理解。问题难就难在这里,禅宗的法,一但成了可以理解的,便立即成了“著相”,成了“知解宗徒”而非“本分道人”,要在自己“本分”上‘“顿悟”就极为艰难,甚至不可能了。
人们的这个心真是说不清楚,对常人而言是烦恼生灭心,对佛菩萨而言是菩提真如心,差别那么大,怎么会是“无差别”的呢?怎么会是“一”呢
自己就是一切,就是成佛的依据,这个力量是如此之大,对被局限在狭小天地中的那个“小我”而言。一旦从中透出,其功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四祖道信大师在十四岁。那年参礼三祖僧璨大师求法时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三祖说:“谁缚汝?”四祖说:“没有人缚我啊!”三祖说:“既然没有人束缚你,又何必去求解脱呢?”就这么简单,四祖就下悟了。
再如石头希迁禅师时,有个叫尸利的学生问他:“怎样才是与他人不相干,完全绝对的属于自己的‘本分事’呢?”石头禅师说:“你要问的是你的那个‘本分事’,这可与我无关,问到我这儿来就不是你的那个绝对的‘本分事’了。”尸利又问;“如果不经老师的点明,我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那个‘本分事’呢?”石头禅师说:“好,我问你,既是绝对属于你的那个本分’,它能丢失得了吗?”尸利在这里于是有所悟入。
再如有个和尚问药山禅师:“怎样才能不被各种外界环境所迷惑呢?”药山禅师说:“外部环境是外部环境。它哪里妨碍着你呢?”这和尚说:“我就是弄不清楚这点。”药山禅师说:“好道,是你自己有所迷惑,怎么能责怪外部环境呢?”这就是迷悟由心不由境的道理,人们若能冲破这道关口,天下没有不明白的道理。
心与境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上面这则公案从一个角度说,下面这则公案又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结合对照,很能有所启发。
有个和尚问怀让禅师:“如果把铜镜铸成一尊佛像,镜子原有的功用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怀让禅师反问他说:“那你小时候的相貌,今天又在什么地方去了呢?”那个和尚又追问:“为什么铜镜铸成佛像后就不能作镜子使用了呢?”怀让禅师的回答极其透彻明了,妙不可言:“虽然不能再作镜子使用了,但万物本来是什么样的,对铜镜或铜佛像而言,还是什么样的,既用不着去改造,也不会受到欺瞒的。”所以,能还万物本原的人,才能还自己的本原。当精神被精神的内容所困绕时,又怎能发挥它的最佳功能呢?同样的道理,人类只有放弃对大自然的粗暴干予时,大自然才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同时人类也才能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认识,有时的确显得是多余的。
“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佛教的法,不论中观唯识。大多说理严密细致。只要不带世俗偏见,都是有路径可以通达的。禅宗以无法为法,但禅师们有上堂的开示、小参、晚参、机锋、棒喝、转语、公案、参话头等种种作略。其中许多仍然是有理路可寻,可以使人理解,如六祖的《坛经》、黄檗的《传法心要》及许多禅师的《语录》等;难解或不可理解的大多为棒喝、机锋和转语,但若经说破,也不是不可理解。问题难就难在这里,禅宗的法,一但成了可以理解的,便立即成了“著相”,成了“知解宗徒”而非“本分道人”,要在自己“本分”上‘“顿悟”就极为艰难,甚至不可能了。
人们的这个心真是说不清楚,对常人而言是烦恼生灭心,对佛菩萨而言是菩提真如心,差别那么大,怎么会是“无差别”的呢?怎么会是“一”呢

自己就是一切,就是成佛的依据,这个力量是如此之大,对被局限在狭小天地中的那个“小我”而言。一旦从中透出,其功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四祖道信大师在十四岁。那年参礼三祖僧璨大师求法时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三祖说:“谁缚汝?”四祖说:“没有人缚我啊!”三祖说:“既然没有人束缚你,又何必去求解脱呢?”就这么简单,四祖就下悟了。
再如石头希迁禅师时,有个叫尸利的学生问他:“怎样才是与他人不相干,完全绝对的属于自己的‘本分事’呢?”石头禅师说:“你要问的是你的那个‘本分事’,这可与我无关,问到我这儿来就不是你的那个绝对的‘本分事’了。”尸利又问;“如果不经老师的点明,我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那个‘本分事’呢?”石头禅师说:“好,我问你,既是绝对属于你的那个本分’,它能丢失得了吗?”尸利在这里于是有所悟入。
再如有个和尚问药山禅师:“怎样才能不被各种外界环境所迷惑呢?”药山禅师说:“外部环境是外部环境。它哪里妨碍着你呢?”这和尚说:“我就是弄不清楚这点。”药山禅师说:“好道,是你自己有所迷惑,怎么能责怪外部环境呢?”这就是迷悟由心不由境的道理,人们若能冲破这道关口,天下没有不明白的道理。
心与境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上面这则公案从一个角度说,下面这则公案又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结合对照,很能有所启发。
有个和尚问怀让禅师:“如果把铜镜铸成一尊佛像,镜子原有的功用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怀让禅师反问他说:“那你小时候的相貌,今天又在什么地方去了呢?”那个和尚又追问:“为什么铜镜铸成佛像后就不能作镜子使用了呢?”怀让禅师的回答极其透彻明了,妙不可言:“虽然不能再作镜子使用了,但万物本来是什么样的,对铜镜或铜佛像而言,还是什么样的,既用不着去改造,也不会受到欺瞒的。”所以,能还万物本原的人,才能还自己的本原。当精神被精神的内容所困绕时,又怎能发挥它的最佳功能呢?同样的道理,人类只有放弃对大自然的粗暴干予时,大自然才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同时人类也才能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认识,有时的确显得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