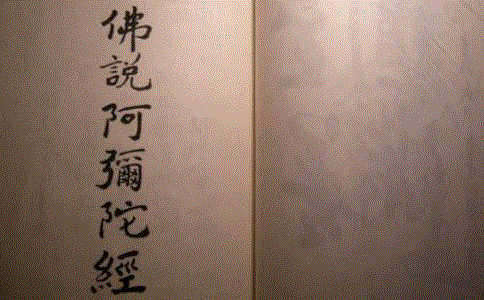评《新雨》的〈谈龙树的哲学〉
发布时间:2022-09-30 17:25:32作者:阿弥陀经全文网评《新雨》的〈谈龙树的哲学〉
龙树菩萨的历史评价
龙树菩萨诞生于佛陀以后六、七百年,佛教史家称他是‘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乘论师。\’[注一]中国佛教受他的影响很大,誉为大乘八宗的共祖,三论宗、禅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和律宗,都自认为受到他的很大启发[注二],因此他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备受崇敬。西藏佛教也深受他的影响,‘中观见\’被视为最究竟、最正确的佛教哲学[注三]。可以说,龙树在北传佛教中的崇高地位是早有定评的,很少人会想到要去重估他的地位和价值。至于南传佛教,由于在西元前二、三世纪传入锡兰之后,就脱离印度佛教史的脉络而独自发展[注四],因此不受龙树菩萨的影响。近代世界交通以来,南北传佛教终于在世界领域内碰面,彼此都自然会有一新耳目之感;相互学习,彼此切磋应该是谦虚为怀的佛教修行人自然会有的态度,所以相信北传的大乘佛教徒也会乐意听听南传上座部的人如何看待他们所崇敬的龙树菩萨。
《新雨月刊》第五三期(一九九二年元月出版)刊出了一文,主答者是一位锡兰籍的比丘净律法师。该刊在中说此文‘略谈龙树的中观哲学的内涵及作用,有助于如实地定立龙树的哲学’,该文的也称它‘有助于使龙树哲学清晰且明朗的定位\’,可见‘给龙树哲学一个定位\’是《新雨》刊出此文的主要企图,相信许多大乘信徒都是愿乐欲闻的。
然则我们看到,在访问中,净律法师自己承认,在锡兰或泰国,‘只有在大学里\’的人才研究龙树哲学,而且‘没有人修学龙树的方法\’时,我们难免有些失望。著名的西方宗教家史怀哲说过:‘没有实践的宗教与道德,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同样的道理,没有透过实践的努力,应该很难了解一个宗教法门的内涵、义蕴和作用。以净律法师的宗教背景和对龙树哲学的涉猎程度,我们很难期望他对中观哲学能有比较深入的认知。但这并不影响他有一分认知说一分话,然而我们却发觉他的口吻与态度太过权威了,例如回答‘只采用龙树的学说,能不能获证涅槃?’的问题时,我们看见的是毫无保留的断定式的回答:‘不可能!’我们就不禁怀疑他的态度是否客观?有没有谨守学者应守的分际?
当然我们不应以人废言,或许净律法师是聪敏的宗教天才,宗通说通,见微知著,虽然对龙树哲学涉猎不深,但他的评价也可能是确当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贸然否定他的话,而应该静下心来听听他怎么说。通观全文,净律法师对龙树中观哲学的评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佛教本来只重视实践,到龙树才把佛教哲理化,这是为了因应当时印度社会风气的需求。二、龙树哲学的哲理思辨,对于体证涅槃只具有一些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助益。前者涉及佛教史实和龙树创作《中观论》的动机,后者则涉及解脱道的理趣,都可以一谈。
佛教与哲理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净律法师说:‘佛教本是个重视实践的宗教,但当时的人们重视哲理思辨,佛教若不谈这些就不能受到重视,于是龙树就出来把佛教哲理化了。’这句话包含两个判断,一是‘本来佛教只重视实践,而没有哲理化。’二是\‘直到龙树才开始将佛法哲理化。’这两个判断都不符合佛教史的常识。
所谓‘哲理化\’可以定义为:‘用抽象的、理论化的语汇,建立有体系的理论,以说明宇宙人生的情况。’如果这个定义可以获得共许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原始佛教的典籍中,早已具备哲理化的条件了。‘五蕴\’‘四识住\’‘缘起\’‘无我\’‘涅槃\’这些常见于阿含经中的语汇,任谁也不能否认它们是相当抽象化、理论化的语词。在《杂阿含经》中随处可见的句子:‘无明缘行,行缘识……’\‘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五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等等也都是相当哲理化的陈述;至于原始佛教的核心教义,如‘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等等,也都是体系整然的理论。因此,说佛法最初没有哲理化,并不符合原始佛教典籍给我们的印象。
有人或许会辩解说,原始佛教当然有一些哲理化的倾向,但是并没有像龙树那样‘致力于\’佛法的哲理化。但是佛教史知识告诉我们,把佛教哲学作进一步整理、发扬的也并非始于龙树。印顺法师等佛教史家的研究显示,着重法义分别的学系早已活跃于早期佛教中,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上座部系的阿毗达磨论书[注五]。南传上座部的七论和说一切有部的一身六足乃至《大毗婆沙论》的完成都在龙树以前[注六]。亦即在龙树之前,佛教的阿毗达磨哲学早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了。净律法师把佛教的哲理化视为忽焉而生的东西,并把它推给龙树,是相当昧于史实的讲法。
净律法师对龙树创作中观论的动机作了如下的描述:‘龙树学说的崛起,是基于社会环境的需要。当时的哲学思想界竞争很激烈,佛教在这方面若没有杰出的表现,就很难受到重视,于是龙树把佛教的道理用很高超的哲理方式表达出来了。’净律法师认为龙树是为了因应时代风尚而用哲理来\‘包装’佛法。如前所述,佛法之哲理化源远流长,在龙树之前小乘阿毗达磨哲学已极为发达,所以‘用哲理包装佛法\’不可能是龙树创作《中观论》的动机。要问龙树的动机,不如来看《中观论》的皈敬颂:‘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注七]阐明佛说的真义,息灭诸戏论,才是龙树的动机吧!我们看龙树在论中所评破的对象,也包括了小乘阿毗达磨论师的见解[注八],就能够明白龙树的用意绝非仅仅于‘包装佛法\’而已,他还有评破小乘迷执,回复佛法正义的用意,《中论青目释》就说:‘佛灭度后,后五百岁像法中,人根转钝,深着诸法,求十二因缘、五阴、十二入、十八界等决定相,不知佛意,但著文字……龙树菩萨为是等故,造此《中论》。’[注九]
思辩与涅槃
第二个问题,是否哲理思辨对体证涅槃没有什么积极的助益?净律法师一再强调思辩的无用,他说:‘把佛法变成逻辑式的,会吸引人去作内心的思辨,但若要使人领悟“法”,逻辑并不是一种好的方式,要体验“法”必须透过对自我内心的了解。’读这句话时我们不禁怀疑,不透过‘内心的思辨\’如何达到‘自我内心的了解\’?这二者如何分得开?《杂阿含经》中不是常常说到‘独一静处,思惟观察’[注一○]才能够体证佛法吗?
他又说:‘你若只管实修,须经很长的时间才会开悟,但若只研究道理,则永远不会开悟。’显然,净律法师把‘实修\’和‘研究道理\’分开来。但是《杂阿含经》不是说:‘我以知见故得漏尽,非不知见。’[注一一]吗?不研究道理,怎能获得‘知见\’呢?修学佛法的过程,经中归纳为‘闻、思、修、证\’[注一二]。闻思都是‘研究道理\’,‘修\’则是把道理和身心作更深密的契合与观察思惟,如此,怎么能说‘研究道理\’与修行绝对无关呢?所以我们很难设想净律法师没有‘研究道理\’,没有‘作内心的思辨\’的‘实修\’究竟是在修什么?相反的,他所否定的透过‘研究道理\’,进而‘作内心的思辨\’其实这才是佛法修行的正常次第。李元松老师深受龙树中观的影响,近期所讲的‘冥想二十次第\’及本刊二五期发表的一文[注一三],对此都有详尽的说明。甚至南传上座部所宗依的《清净道论》也应该不离这个原则吧!
净律法师否定透过龙树的思想可以取证涅槃,他的理由是:‘因为单靠逻辑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透过《杂阿含经》中一些直接经由佛陀或善知识的开示说法而当下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所用的方法常是反诘式的,一个问题扣着一个问题的深入,终于使闻者顿见法性,现观涅槃[注一四]。所以恰恰相反,有条理的思辩程序,可以是使人由迷转悟的一种方法,端在使用者是不是明眼人。得法眼净,证初果,是取证涅槃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关卡,在这个关卡中,逻辑思辩可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另外,净律法师之所以认为龙树哲学是无用的,又有一个理由是‘龙树所说的是已解脱者的境界\’‘我若是已开悟解脱者,龙树的学说在我看来是完美无瑕的,但我已不需要它;我若是尚未开悟解脱者,龙树的理论又派不上用场。’这样的讲法,一方面把龙树哲学讥为炫耀式的无益玄辩,另一方面也显示净律法师完全不了解‘果地见\’在解脱道中的力用。龙树曾说:‘为可度众生,说是毕竟空。’[注一五]若非为了引导人们体证涅槃,所谓‘完美无瑕的理论\’只是无益的戏论而已。众所周知,《中论》以破斥邪见著称。破斥邪见,何必对已无邪见的解脱者说呢?而破斥邪见竟然会对‘尚未开悟解脱者完全派不上用场\’吗?
按图索骥的修行方式
《中论》阐扬的是无我空义。《杂阿含经》说:‘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注一六]可见即便依据阿含之教,无我正见也是契入涅槃的正因。所谓‘尚未开悟解脱者\’,也就是不了解‘无我正见\’的人,对他而言,破斥迷执,显扬无我的中观教法,难道不是他转迷成悟时所必需的?而净律法师对此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论断。他的修行观是:‘只要你自己修学佛法,像修戒、定、慧,你自然会体悟到龙树所说的。’但\‘采用龙树的学说’却\‘不可能获证涅槃’。显然净律法师鼓励的是一种一个人蒙着头按图索骥的修行方式,并认为明眼善知识或解脱者的自内证对凡夫没有任何的帮助和作用。小乘阿毗达磨论整理阿含经中所说的修行次第,固然有一定的页献,但若执成定局,按图索骥,并且拒绝解脱者来自妙高峰上的法音,那么恐怕就不是善巧的修行观了。净律法师说:‘佛法就像一门科学,’接着又说:‘你若只管实修,须经很长的时间才会开悟,但若只研究道理,则永远不会开悟。’这就好像说,一个人想要了解‘相对论\’这门科学,却拒绝研究爱因斯坦所得的结论,反而研究起爱因斯坦的生平和他读过的书,并认为只要‘只管实修(照着做)’,终有一天一定会明白相对论的;同时却又主张直接研究相对论的道理,则永远不会懂相对论,因为科学就必须这样学,这是多么荒诞的学习观呢?
印顺法师对南传上座部佛法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评论:‘释尊住世时的佛教,我也承认比较上接近巴利文系的佛教。或者觉得它既然接近佛教的原始态,佛教徒只要忠实的依着它去行就得。……巴利文系的佛教者,虽自以为是理智的佛教,说大乘是感情的佛教;在我看来,他们只是依样葫芦的形式崇拜。他们根本的缺点,是忘却佛教是哲者宗教之一;哲者宗教应怎样去信仰它,从来没有理会过。’[注一七]此文虽写于三、四十年以前,但与净律法师的修行观对比起来,仍觉其虎虎有力,切中其弊。
正确理解龙树思想
谈完上述两个问题,本来可以结束对净律法师之见解的讨论,但是由于一文,是净律法师和新雨同人的对话录,其中还牵涉到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再说几句。
其一是、他们和净律法师曾试图讨论‘把他的方法实践化\’的可能性,而终于不了了之。其实,龙树菩萨的著作很多,有‘千部论主\’之称,一些佛教史著作都说明龙树学说的全貌包含了‘深观\’和‘广行\’两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如《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菩提资粮论》等等都是广明菩萨大行的[注一八]。也就是说,龙树的‘深观\’如何‘实践化\’,如何结合‘广行\’,龙树自己早就有了详尽的解说,因此这并非隐晦不明的问题,而净律法师‘停顿、沉思\’之后,仍然无法想像如何将龙树中观实践化,只说:‘龙树说,不执着于二边,即使中道亦不可执着,这一点很难解释。’足见他对龙树学说的完整性并不了解;不见龙树学说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就将他贬斥为贫乏、没有实践化的玄谈,就好像一个不懂书法的人,竟然说苏东坡的是乱写的,一样的不恰当。
其二是他们三人在讨论中共许龙树没有提供特定的方法以引导人们趣入涅槃,甚至形成了龙树主张‘没有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这个结论。我们且不谈龙树其他论及‘广行\’的著作,光以《中论》的内容来说,其实《中论.观法品》就曾明确的指出:‘灭我我所故……,名得无我智,得无我智者,是则名实观。得无我智者,是人为希有。内外我我所,尽灭无有故,诸受即为灭,受灭则身灭,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注一九]又说:‘如来过戏论,而人生戏论,戏论破慧眼,是皆不见佛。’[注二○]息诸戏论,得无我智,是《中论》明确提出的趣入涅槃的方法,与前引《杂阿含经》‘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的经义若合符节,因此怎能说龙树没有提供方法,甚至推论出龙树主张‘没有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的结论呢?这是对龙树中观哲学的一大误解。
其三是净律法师说:‘释迦牟尼佛教导人的方式,是有法次法向的,由世俗谛逐渐提升到最高的第一义谛。’他认为是龙树的空观哲学毁弃了这一切,他说:‘他教人舍弃一切,一切法不可执,连佛法、佛陀以及他的教法皆不可执。’从这里,我们仿佛看到大乘经中提到的‘闻空义则心如刀割\’的小乘人的心声。其实龙树的中观并不否定佛陀的教法。对于有这样误解和担心的人,龙树曾慰勉他说:‘汝今实不能,知空、空因缘,及知于空义,是故自生恼。’[注二一]在中,龙树说明了‘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注二二]的道理,详细论证了‘只有空义才能够建立整个佛法理论,若不成立空义,则佛法理论也无法建立’的道理。因此读过《中论》的人都不应否认龙树以空义来成立四谛、三宝、罪福因缘的事实,而用龙树不曾犯的错来指责他。至于《新雨》的中,引用龙树《中论》‘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注二三]一语来提醒龙树学的行人,也令人有错愕之感。
其四是他们三人在讨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包括三法印、四圣谛在内,佛陀的一切教法‘都只是帮助人们的工具而已,并不是究竟的真理。’在中,编者也显然把四圣谛、八正道归属于‘俗谛\’。我们在《新雨》中读到这样的论断,无疑是令人惊异的。据我们所知,《新雨》和小乘上座部执都一向把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等等说成‘是谛、是如、是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胜义谛;怎么突然之间南传上座部的法师和《新雨》同人改变了这个重要的基本教义了呢?我们认为这个改变是属于教义的全盘性的改变,甚至可说是回归中观的立场了,似乎不应轻忽为之。倘是严谨的有一贯主张的弘法团体,似乎有必要正面说明这种根本性改变的理由。
其五是此文肯定‘龙树所说的是已解脱者的境界\’。记得《新雨》在以前刊载的文章中,曾经痛骂龙树哲学是‘佛魔同体论\’‘是非不分论\’的邪见,并且支持这样的说法,今昔对比,无异于南辕北辙。关心《新雨》的朋友难免怀疑,到底《新雨》对龙树的真正看法是什么?如果《新雨》的看法确实转变了,也应该明确地向读者说明。如果《新雨》自己也依违两可,毫无定见,就显然对自己刊物发表的文章和自己的言论太不负责任了。《新雨》是佛教界少数致力讨论修行问题的刊物,值得大家肯定,所以我们对他也就有一些起码的期许,相信《新雨》也会注意及此才是。
注:
注一:参考吕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台北,天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初版,改名为《印度佛学──思想概论》),一一○页。
杨白衣,《印度佛教史略》,台北,普门文库,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五八页。
松本史郎,。(收入山口瑞凤等着,许洋主译,《西藏的佛教》,台北,法尔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初版,二三三页。)
干潟龙祥,,(收入水野弘元等着,许洋主译,《印度的佛教》,台北,法尔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版,二一六页。)
参阅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第二章,作者自印,一九七八年四月再版,四三──九○页。
同前注,二一二页。
《中论》卷一(大正三十.一中)
印顺,《中观论颂讲记》,台北,正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十版,三三页。
《中论》卷一(大正三十.一中下)
《杂阿含经》卷八(大正二.五一中)
《杂阿含经》卷十(大正二.六七上)
《俱舍论》卷二二(大正二九.一一六下)
见《现代禅杂志》第二五期,一九九三年一月。
可参阅拙著,已收入本书。
出自《大智度论》,转引自印顺《中观论颂讲记》,四七○页。

《杂阿含经》卷十(大正二.七一上)
印顺,《华雨香云》,台北,正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九版,二四五页。
吕澄,前引书,一一七页。又印顺《中观论颂讲记》,二页。
《中论》卷三(大正三十.二三下)
《中论》卷四(大正三十.三○下~三一上)
《中论》卷四(大正三十.三二下)
《中论》卷四(大正三十.三三上)
《中论》卷四(大正三十.三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