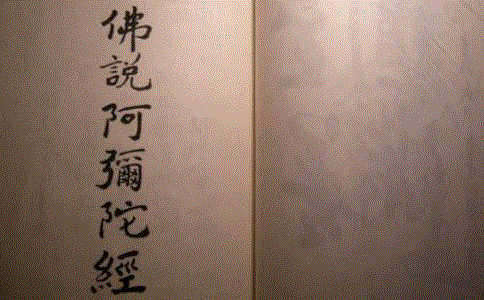听张焯讲云冈石窟,现场只能用“火爆”形容
发布时间:2024-07-24 03:37:50作者:阿弥陀经全文网9日下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迎来一场特别的讲座:由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讲坛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汾讲堂联合主办、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支持的讲座“云冈石窟——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正在举行。主讲嘉宾为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云冈旅游区管委会主任张焯。无论是讲座期间还是互动环节,现场气氛可以用“爆棚”来形容。山西晚报新媒体平台进行了直播,截至记者发稿前,观看量已近10万。讲座由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和山西晚报副总编辑吕国俊联合主持。
这是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讲坛成立以来组织的第三场讲座。讲座前两天,山西晚报·文博山西开通微信报名通道后,报名者短时间内就达到二百多名,最后不得不限制名额。参加活动者,既有从北京、杭州专程赶来的,也有从“云冈的故乡”大同一路跟到太原的。来自不同地域和行业的百余听众,将现场挤得满满当当,过道里、讲台下、大门口,到处都挤满了人。座位不够,有人就席地而坐,也有人自带小板凳,还有人站着听完了讲座全程。“公众对山西文化、云冈文化和艺术的热爱,真是太直观也太惊人了。”来自杭州、老家在山西的常先生站了两个多小时听完讲座后感慨地说。
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佛教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齐名。石窟规模宏大,造像内容丰富,雕刻艺术精湛,形象生动感人,堪称中华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作为云冈石窟研究院的院长,张焯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极为精深。讲座中,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佛教东传的波浪式轨迹”“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因缘”“东方佛教艺术的旷世绝唱”“平城时代对中国佛教的重大贡献”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解读了云冈石窟的博大精深。
讲座末尾,张焯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提问者踊跃异常。云冈石窟研究院还为每个提问者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即由张焯院长主编的《中国石窟艺术——云冈》,现场气氛因这个小惊喜更加热烈,听众争先恐后地提出被张焯院长称为“极专业”的问题。讲座结束了,大家还围在他身边不断提问和签名,久久不肯离去。
来自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李安红教授告诉记者,“我从事雕塑专业方向,在教学中经常到云冈石窟进行艺术考察,学习雕塑艺术的样式等。今天有幸聆听张焯院长的学术讲座,听他详细阐述云冈石窟的形成、艺术成就和其中蕴含的佛教文化和中西方文明交融,受益匪浅。”一位观众还在朋友圈发文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一边看PPT上张张佛像静美脸庞的图片,一边听张老师对佛教、对佛像艺术的讲述,真是种享受!之前对此了解的碎片被完美地连接起来,有些朦胧的认知也豁然开朗!这是云冈的魅力,张老师的魅力!感谢晚报让我知道这个含金量爆棚的讲座信息。”
活动最后,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还为张焯院长颁发了“文博山西智库专家”聘书。
嘉宾档案张焯
现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云冈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文博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学中心客座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宗教艺术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硕士生导师。山西省五一劳动模范、山西旅游业十大功勋人物、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高端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8年6月被授予“2016-201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为全国仅有的七位“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之一。本报2018年6月“封面人物”曾进行专题报道。
云冈石窟,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
在遥远的东方,五世纪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佛教的兴盛与云冈石窟的开凿,是西来像法在华夏大地奏响的一曲惊世乐章。
4月9日,在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讲坛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汾讲堂联合举办的讲座上,张焯院长对此进行了精彩解读,本报特辑选部分精彩要点,以飨读者。
佛教东传的波浪式轨迹
佛教创始于印度,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涅槃于公元前五世纪,与中国的老子生活于同一时代。释迦牟尼的生前死后,佛教主要传播于印度的恒河中游一带。阿育王时期大力弘扬佛法,之后佛教向北发展进入中亚地区。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使印度佛教与犍陀罗当地神学以及希腊神学合二为一形成大乘佛教,由此向外发展进入新疆。
中华佛教始传于东汉,酝酿于魏晋,勃兴于十六国,鼎盛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复兴于宋辽金元,衰落于明清。十六国南北朝是关键。
佛教西来的途径有二:西南海路与西北陆路。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四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实得益于五胡十六国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机缘。
新疆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新疆的佛教在公元一、二世纪已发展到了鼎盛,汉地佛教发展稍晚。学界对汉地佛教兴起具体时间有以下几种说法:秦始皇时期、王莽时期、东周时代等,但主流观点认为是在东汉明帝时期。
佛教的大发展是随着五胡乱华而来的。后赵石氏父子拜佛图澄为师,中国佛教发展迎来第一个高潮

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因缘
道武帝建都平城,任命高僧法果为道人统,管摄僧徒。“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在此之前,西域胡僧入华,奉敬其佛,无须礼拜皇帝。法果提出的帝佛合一的新理论,迎合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需求,使宗教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奠定了北朝佛教鼎盛的基础。后来的北魏僧统师贤为文成帝立像“令如帝身”,昙曜在武州山为五位皇祖开窟造像,实属法果理论的再创造和付诸实施。
从道武帝建国,到太武帝结束北方纷争,北魏推行的各项政策,使平城迅速跃升为北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对西域的征服,又将平城推向东方国际大都市的新高峰。439年灭北凉,徙凉州吏民三万户,“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平城随即成为中华佛教的新中心。
鹿苑,全称鹿野苑,即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说法成道处,在今印度贝拿勒斯城郊。北魏鹿苑,在平城皇宫北,道武帝天兴二年(399)起筑。平城鹿苑与印度鹿苑,在僧众的心目中自然成双,产生共鸣。昙曜五佛的横空出世,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献文帝拓跋弘,坚定了他追仿西天胜迹,建立东方鹿野苑的信心。武州山石窟寺建设全面展开。
北魏对西域的征服,直接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平城迅速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印度石窟造像之风,经由新疆,波及河西、关陇,至平城而特盛,进而流布中华。
东方佛教艺术的旷世绝唱
关于云冈石窟的艺术源流,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论述颇丰,其中最为流行有犍陀罗艺术、马图拉成分、新疆风格等观点。
云冈石窟开凿大致分为三期,早期为文成帝时昙曜五窟的开凿,中期为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晚期为迁洛后民间补刻的窟龛。
云冈早期佛像与印度、新疆艺术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从佛法东传的时代背景分析,凉州僧匠最初带到平城的只能是凉州模式或西域样式。新疆式的犍陀罗艺术甚至马图拉艺术,移花接木般地在云冈石窟翻版,应当属于历史的必然,尤其是大乘佛教盛行的于阗、子合等地像法。从云冈石窟的工程本身分析,凉州僧匠是规划设计的主体,匠僧主体是来自中原各地的汉人,因而大量运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雕刻技艺和表达方式。西式设计与中式技艺是云冈最大特点。越往后来,中华传统的分量越重,自主创新的意识越强。这就是云冈造像艺术并不简单雷同于印度、中亚、中国新疆等地的原因。
云冈石窟中期,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蓬勃发展阶段。一方面是西来之风不断,胡风胡韵依然浓郁,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汉式建筑、服饰、雕刻技艺和审美情趣逐渐显露。与早期造像相比,中期造像健硕、美丽依旧。太和十年(486)后,佛装、菩萨装向着汉族衣冠服饰转化的倾向,显然是孝文帝实行服制改革、推行汉化政策的反映。
云冈晚期洞窟,类型复杂,式样多变,四壁三龛及重龛式是这一时期流行的窟式。佛像一律褒衣博带,面容消瘦,细颈削肩,神情显得飘渺虚无;菩萨身材修长,帔帛交叉,表情孤傲。给人以清秀俊逸、超凡脱俗的感觉,显然符合了中国人心目中对神仙形象的理解。造像衣服下部的褶纹越来越重叠,龛楣、帐饰日益繁杂,窟外崖面的雕饰也越来越繁缛。上述风格与特征,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同出一辙,标志着中华民族对西来佛教像法的引进与吸收过程的初步终结。
平城时代对中国佛教的重大贡献
北魏定都平城的九十七年,是中国佛教成长壮大、方兴未艾的关键时期。北魏肇建的云冈石窟直到唐代以前,都是中国唯一的大型佛教石窟艺术宝库。除了云冈石窟对于后世石窟建设、美术发展的影响之外,此间引进、形成、确立、巩固的佛学思想,以及僧官体制、僧尼制度及寺院经济模式,对后世佛教发展影响深远。
北魏平城时代中华佛教中心的形成与确立,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至于平城佛教与艺术对高句丽、日本国的影响,也逐渐为世人所认知。本版采写:山西晚报记者南丽江实习生李倩楠
视频拍摄:山西晚报记者 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