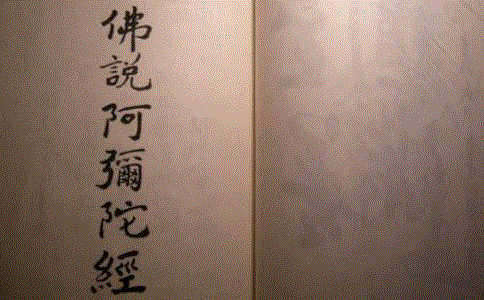《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与明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二)
发布时间:2023-09-23 03:20:56作者:阿弥陀经全文网一、《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的版画内容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中的版画作品主要由《诸佛世尊妙相番相名号》中的63幅版画、《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赞经》中的22幅版画和《三十五佛名经》中的36幅版画组成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部分佛像名称的汉译体现出元、明时期的特点,如“坏相金刚”和“金刚勇识”等,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现在通行的译名之一。但是,其中也有部分译名与现行通用的译名不同。如:“尊圣佛母”,现在通行的译名为“尊胜佛母”;“伞盖佛母”,现在通行的译法为“白伞盖佛母”或“大白伞盖佛母”;“树叶佛母”现在一般译为“叶衣佛母”;“六十二佛”现在一般译为“胜乐金刚”或“上乐金刚”;“吉祥菩萨”一般译为“象鼻天”;“马哈葛辣”一般音译为“马哈葛剌”、“玛哈葛剌”等,更多则意译为“大黑天”;“宝王菩萨”一般译为“布禄金刚”;“宝藏菩萨”一般译为“黄布禄金刚”或“黄财神”;“马项忿怒”现在通行的译法为“马头明王”或“马头金刚”;“不动忿怒”则通行译为“不动明王”;“韦驮尊天”,现在一般都译为“白色不动明王”。这些译名虽然大多未能沿用至今,但体现出译名发展的历程和时代的一些特点,对于元、明时期汉译藏传佛教典籍的阅读和研究无疑有所帮助。
二、版画的艺术特点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中的这些木刻版画均为黑白单色版画,规格大致有两种:一种较大,规格为20x14厘米,占据了整幅页面(参见图2、6-8);另一种尺寸较小,为13x10厘米(参见图1、3-5),为绝大多数版画流行的规格。这些作品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仅代表了明代藏传佛教木刻版画艺术的杰出成就,而且也是明代藏区和内地整个藏传佛教版画艺术创作的一个完美的缩影。从中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藏区版画艺术创作的面貌,而且也可以领略到内地汉式版画艺术的神韵。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自西夏以来内地藏传佛教版画创作发展的重要结晶:汉藏和藏汉艺术的水乳交融。因为在艺术上,这些木刻版画作品明显地体现出三种互有关联而又不同的风格。其中,第一种是受内地因素较少、藏式风格突出的版画,第二种是典型的汉式风格版画,第三种是受藏式因素较少、汉式风格突出的版画。
1.藏式风格突出的版画
藏式风格突出的版画作品是《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中收录的版画主体,主要包括《诸佛世尊妙相番相名号》中的63幅版画(参见图1-2)、《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赞经》中的22幅版画(参见图4)和《三十五佛名经》中的36幅版画(参见图5)。
从风格上来看,这些藏式版画虽然在构图、人物造型和装饰纹样等方面都基本保持一致,但仔细观察,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变化。这些不同的变化,按构图、人物造型、背光和莲座大致可以细分为如下两类:
1)造型精美,装饰繁复
这一风格的作品主要是《诸佛世尊妙相番相名号》中的前三幅作品,亦即四臂观音、文殊菩萨(参见图2)和释迦牟尼佛。在题材上,释迦牟尼佛版画表现的是一佛二弟子,而文殊菩萨和四臂观音表现的则是单尊造型;在构图上,除释迦牟尼佛略为不同外,其余二者相同。将佛与菩萨构置在完整的大型背光和宝座之中是这一风格版画显著的构图特点。中心主尊人物的刻画比例协调,造型庄重、典雅,肃穆之中不乏慈睿的表现。四臂观音和文殊菩萨均为坐式造型,菩萨装束、面部圆润、丰颐,弯眉低目,樱桃小唇,高髻,头戴五叶冠;丰胸细腰,上身裸露,双肩披帛;下著短裙裤,其上绘满精美、繁复的花纹;佩戴精致的耳珰、臂钏、手镯、脚镯和繁复的项链。整个造型和装饰传递出几许女性的柔美。与此相对,释迦牟尼佛则展示出健壮的阳刚之美。释迦牟尼佛也为坐式造型,为佛装,螺发高髻,袒露右肩,身著百衲袈裟,尤其是俯视有神的双眼的刻画、圆润的双肩和宽实的胸膛的表现以及健壮有力的右手的表现,充分体现出释迦牟尼佛追求成佛的坚毅和信心。背光正中的上方、亦即佛与菩萨的顶部为大鹏鸟,其下左右两侧的台座上分别构图有一只摩羯鱼,摩羯鱼的尾部如缠枝纹一样,艺术化地形成两道对称的圆圈,与大鹏鸟喙中所含双蛇的身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台座之下,从上到下,分别构图有狮羊、狮子和大象等三只瑞兽,左右对称。这些瑞兽在十八世定型成六拿具。在左右三对瑞兽的中心、亦即佛与菩萨的下方,构图的是莲花座。莲花座呈椭圆形,由仰瓣和覆瓣莲花组成,莲瓣巨大,瓣尖状如如意云头,造型朴素大方。在莲花座下方,构图的是工字形的须弥宝座,其上精雕细琢,装饰有动物、植物和珠宝等各种纹样,其中在宝座的上层中央,悬瀑着一块绘有莲花纹样的盖布,十分醒目。中心的人物均饰马蹄形身光和桃形头光,二者除边缘一周饰有纹样外,均为素面。整个构图完整、对称、协调,一气呵成,装饰精美、繁复,线条的勾勒流畅,如行云流水,起承转折富于变化,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在构图上,三幅作品的不同之处是,在释迦牟尼佛版画中,其两侧的立式弟子取代了四臂观音和文殊菩萨版画中背光两侧的三对瑞兽。
通过类比,这3幅作品的风格显而易见受到了元代内地版画艺术传统的直接影响。我们不仅在元代《碛砂藏》和《普宁藏》大藏经的木刻版画中找到与此相似的风格,而且发现二者的某些构图和造型都如出一辙,例如此处释迦牟尼佛一佛二弟子的构图与《普宁藏》“教主释迦牟尼佛说经处”版画中心部分的构图完全一致。与此同时,这三幅作品的宝座和背光,除其中的瑞兽和部分装饰纹样不同外,也与《碛砂藏》和《普宁藏》大藏经的木刻版画极其相似。
2)造型简朴,装饰艺术化
造型简洁、朴素和装饰纹样趋于艺术化,是《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绝大多数版画作品的特点。这些作品包括《诸佛世尊妙相番相名号》的后60幅作品以及《大教王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赞经》和《三十五佛名经》中的所有版画作品(分别参见1、3-5)。
与前一种风格相比,这些版画除主尊人物的表现外,在构图和装饰纹样的表现上都趋于简洁。
首先在题材上,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诸佛菩萨和明王的单尊形象。其次在构图上,精美、繁复的大型完整背光在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简洁的马蹄形大背光;宝座也趋于简洁,只剩下莲花座,并且除《大教王经》中的5幅版画作品的莲花座为双重仰覆莲瓣外(参见图3),其余作品的莲花座均为覆瓣莲瓣(参见图1、4-5)。再次,前一种风格中菩萨装人物胸前佩戴的精美繁复的项链和项圈在此也被简化。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版画背光边缘的火焰纹和背光中的缠枝纹趋于抽象化和概念化,更富有装饰韵味。
虽然这些藏式风格的版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但在构图、人物造型和装饰上仍体现出一种统一的格调。从整体来看,其中尼泊尔艺术的因素十分突出,波罗艺术的特征逐渐消失,而汉式艺术的因素逐步增强。例如,从菩萨装的菩萨和佛母等题材的作品来看,人物的造型及其装饰都具有显著的尼泊尔艺术的特征。人物丰胸、细腰和宽臀的造型,五叶冠和项链、项圈、手镯、臂钏和脚镯的形制都充满了浓郁的尼泊尔艺术的情调。不仅如此,一些装饰纹样的造型也是如此,尤其是背光边缘的火焰纹装饰和背光中的缠枝纹装饰体现出明显的尼泊尔艺术的特征。与此相对,在西夏时期内地版画中比较流行的印度波罗艺术的特征在此几乎消失殆尽,其中唯一的遗韵,如果能够完全确认,就是背光背部背景中装饰的宽大的热带植物(参见图3-4)。与此同时,汉式艺术的特征开始大量出现。实际上,《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版画所体现的这种风格特点,与明代西藏壁画、唐卡和雕塑的特点基本吻合。如以壁画为例,其中许多版画作品完全可以与西藏江孜1418-1436年间创作的白居寺壁画媲美。
这些版画作品所谓藏式风格突出,是指无论诸佛菩萨的构图,人物的造型和装束,还是背光、身光、头光、莲座等装饰纹样都体现出浓郁的藏式风格韵味,但其中也融入了汉式艺术的因素。这些汉式风格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莲瓣的造型、主尊身后背光两侧云纹的表现和背景的补白上。例如,《大教王经》和《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赞经》版画背光两侧的云纹(参见图3-4),《诸佛世尊妙相番相名号》后60幅作品和《三十五佛名经》36幅作品在背光两侧对称装饰的补白花卉(参见图1、5)。其中,利用花卉装饰来补白值得一提。在《诸佛世尊妙相番相名号》作品中,左右对称地装饰有3对花卉(参见图1),而在《三十五佛名经》作品中,只对称的装饰有2对花卉(参见图5)。这些花卉只勾勒轮廓,造型非常简洁,其造型和这种做法应源于内地,在西安出土的唐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画中不仅能看到其雏形,同时在西夏时期的版画中也非常流行。
实际上,除装饰纹样外,部分神灵的造型也受到了汉式艺术的影响,《诸佛世尊妙相番相名号》最后4幅作品四大天王就是其中的例证。与内地传统四大天王的造型相比,这4幅作品的人物造型虽然并不典型,但从此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比较浓郁的汉式艺术特征。以面部造型为例,内地传统的方形国字脸在此虽然有些变化,但其原形仍依稀可辨。五官的特征也是如此,虽然经过改造,但仍似曾相识。头盔、铠甲等装束的表现也是如此,铠甲中内地典型的锁子甲纹样虽然已被替换,但靴子等部分服饰仍体现出内地传统造型的特点。四大天王是藏传佛教艺术诸佛菩萨题材中造型深受内地艺术影响的题材之一。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题材经过历代的不断吸收和融合,已经与藏族文化水乳交融。其造型虽然源于内地,但与内地传统的造型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已经融入了藏族的审美文化。
2.汉式风格版画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除大量的藏式风格突出的版画作品外,其中还收录有两幅典型的汉式风格版画作品。它们分别是《佛说阿弥陀经》插图《西方净土变》(参见图7)和《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插图《水月观音》(参见图8)。
首先,《佛说阿弥陀经》插图《西方净土变》从构图、题材、人物造型、背景和装饰纹样的表现等方面来看,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作品。从构图来看,云雾缭绕的歇山顶宫殿建筑群、中心的一佛二菩萨和其前的水池、化生和人物等安排,为内地净土变题材中典型的远景、中景和近景构图模式。在敦煌净土变壁画和汉传佛教净土变绘画艺术中,这一模式非常流行。从题材来看,阿弥陀佛和胁侍观音和大势至菩萨的组合也是汉传佛教中流行的题材,在藏传佛教中绝少能见。从人物造型来看,一佛二菩萨的造型及其装束,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最后,从纹样来看,亭台、楼阁、栏循、水池、云彩、莲花、宝座和动物等纹样也呈现出一片汉风。不仅如此,这种构图模式在明代内地的版画创作中也非常流行。
与《佛说阿弥陀经》插图一样,《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版画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的作品。从题材上看,水月观音是汉传佛教中常见的题材,而在藏传佛教中绝少表现;从构图上看,作品也是按远景、中景和前景的模式构图;从人物造型来看,观音菩萨、供养天和童子的相貌及其装束与藏传佛教艺术无关,也是定型的汉式人物造型;从背景和装饰纹样来看,风景在作品中具有构图的特殊功能,并非仅为装饰,这是汉式绘画的显著特征之一。不仅如此,山石、云纹、水波、莲花和竹子等风景要素的表现也是典型的汉风。有趣的是,在内地创作的与藏传佛教艺术相关的作品中,《普门品》水月观音题材比较流行。例如,在元代杭州飞来峰1282-1292年间创作的藏传佛教风格的石雕作品和甘肃永登县红城镇1492年修建的感恩寺壁画中都有这一题材的表现。
3、汉式风格突出的版画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除上述两大风格的版画作品外,还有一些汉藏两种风格融合于一体,但汉式风格十分突出的版画作品。这种风格的作品主要是组成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完整画面的4幅《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插图《释迦牟尼说法图》(参见图6)。从总体风格来看,汉式风格在其中居于主导的地位。首先,左、中、右的构图形式是传统内地版画的典型构图形式之一。其特点是中心购置主尊人物,两侧构图胁侍人物。其次,大部分人物的面相和装束是内地汉传佛教常见的形式,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罗汉、四大天王和部分菩萨的造型及其装束非常典型。在此,背景中大量如意云纹的表现和佛座的造型也源于典型的汉式传统。整个风格令人想起唐宋以来的内地佛教艺术。另外,“皇图永固”牌匾从形制到内容都是典型的汉式风格。从形制上看,该牌匾成长方形,由牌匾和基座两部分组成。其中,牌匾部分由中心长方形的文字和四周的装饰图案组成。值得注意的是,装饰部分由四条龙纹组成:顶部为二龙戏珠图案,而主体部分、即文字两侧则由一对对称的升龙组成,并且龙爪为五爪龙。它在此的出现与其中文字内容吻合。牌匾之下为工字型的须弥座。牌匾和须弥座的这种组合在内地佛教文化中十分流行。大约从西夏开始,它出现在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作品中,并且在随后的元、明、清三代的内地藏传佛教艺术中比较盛行。以绘画作品为例,我们不仅在1277-1290年间刊刻的《普宁藏》汉文大藏经和1295-1307年间刊刻的《河西字大藏经》插图版画中找到类似的题材和形制,甚至在洪武年间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南藏》中可以找到造型和文字内容都与此几乎相同的版画作品。与《南藏》等作品唯一不同之处是,在构图上将牌匾融于整个作品之中,同时将其置于作品的右边,而在此则由于排版空间的局限而被独立出来而已。《说法图》藏式风格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右侧版画第一排中心的两位胁侍菩萨和左侧版画第一至二排三位胁侍菩萨的表现上。其中,高而尖锥状的顶髻和简洁朴素的五叶冠造型十分突出,尤其是五叶冠的造型还留有较浓的尼泊尔艺术的遗韵。这一装饰正好与造型繁复、样式截然不同的传统汉式菩萨的头饰形成鲜明的对比。
原文载艾瑞卡?福特、梁俊艳、黛博拉?克林博格?索特、张云、海尔默特?托舍主编:《8-15世纪中西部西藏历史、文化与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