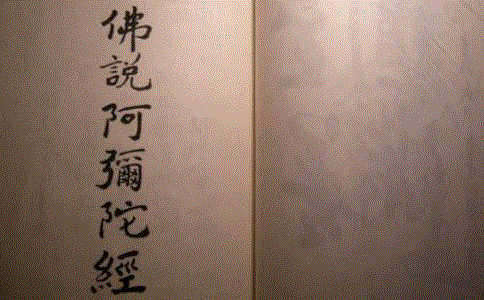曾国藩:从30岁起,脱胎换骨
发布时间:2024-05-15 03:36:40作者:阿弥陀经全文网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
1 三十岁以前是庸人
曾国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乡县大界白杨坪。地处离县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虽山清水秀,风景不恶,但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曾国藩在诗中说这里“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2008年四月,我去探访这个地方,发现它到现在似乎也不怎么需要与外界打交道,班车次数极少。我从韶山出发,居然辗转颠簸了整整一天,换了五次车(包括摩的),才到达这里。在晚清时代,这里的闭塞程度更可想而知。在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之前,几百年间,这里连个秀才也没出过。不但“无以学业发明者”,也没有出现过大富大贵之族,可以说是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角落。
传统时代,农民们想要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几乎只有供子弟读书一途。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后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孙们靠读书走出这片天地。他不惜血本,供长子曾麟书读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然而,曾麟书资质实在太差,虽然在父亲的严厉督责下,兀日穷年,攻读不懈,却连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败了。
作为长孙,曾国藩身上背负着上两代的希望。然而曾家的遗传似乎确实不高明,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也是榜榜落第,接连七次都名落孙山(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也没有一个读书成功)。曾家已经习惯了考试失败后的沮丧气氛,他们几乎要认命了。然而,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的命运之路突然峰回路转。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举人。又五年之后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老曾家一下子老母鸡变凤凰,成了方圆几十里的第一大户。
虽然跃过了龙门,但此时的曾国藩整个眼眶里只装得下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在白杨坪这个小天地里成长起的曾国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过往是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
进京为官以前,曾国藩耳目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当官发财,给家里争口气。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余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结束在家“把戏”,抵达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官宦生涯。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在北京头两年,他用于社交时间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四十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但这个日课并没有严格执行,虽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还是经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门拜客。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日记载,早饭后,张书斋、曾心斋两位朋友先后到他家来聊天。送走他们后,他写了十行字,又出门“拜客数家”。然后又赴宴,与七个朋友一起饮酒吃饭。饭后又去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天所有的“成绩”就是十行字。
翻开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已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爆,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
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然而用圣人标准一衡量,问题就严重了。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并且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2 “脱胎换骨”的操作过程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毅然立志。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中国儒、释、道三家,对生命目标的设计都是极其超绝完美的。道家以为,人通过修炼,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无恃,长生久视,与天地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佛教则以为人皆有佛性,通过自修,都可以达到不生不灭断尽欲望的佛的境界。儒家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圣人理想,其完美与超绝不下于神仙或者佛陀。
儒家经典说,所谓“圣人”,就是达到了完美境界的人。圣人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对内可以问心无愧、不逾规矩,对外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
超自然的夸张固然过于虚幻,不过,除去这些飘渺的因素,儒家的“圣人”理论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着符合人类基本心理经验的合理内核。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层是食色性也,第二层次是安全的生存环境,第三层次是人际交往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功名荣耀、出人头地。最后一个层次是自我实现。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将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烧到最充分,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
儒学的圣人理想,基本上可以类比为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确实,儒家的“圣人状态”与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后的“高峰体验”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所谓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为欲望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而英雄伟人则是醒过来的人,他们天性刚强,头脑有力,可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而“圣人”,或者说达到“自我实现”状态的人,则是通过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欲望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
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到了圣人状态,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感通”。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快的情感状态。而马斯洛也说,当一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时,也会体验到一种难言的愉悦,欣喜若狂、如醉如痴。人在这时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智能。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应该说,儒家的圣人理想远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高远和超越。马斯洛给人实现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间,而儒学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构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圣人理想有着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圣人学说”也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心理武器。所谓“取法乎上”,它确实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调动起全部潜能的奋斗目标。只不过,儒家学说所设定的自我完善目标如此高远和超越,几乎不可操作。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谁坚持的时间长。他对第一群人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人说的是,想看看你们谁最有耐力。对第三群人,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如果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就要断电。为了朋友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多举一会儿。
结果,第一群人平均举了十分钟,第二群人竭尽全力,平均坚持了十五分钟。第三群人,却平均坚持了二十分钟。
可见,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身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大的生命之殿。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
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办法是“日课”。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业”,“闲谈荒功”,“溺情于奕”。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整个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但是,一个人想一下子改个久已养成的生活习惯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曾国藩为人交游广阔,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虽然立下志向,也难免有因为交游影响学习的事发生。
比如当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早起读完《易经》,出门拜客,又到杜兰溪家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参加完婚礼后,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于是又顺便到何家庆生,饭后又在何子敬的热情挽留下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
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对自己下午没能回家用功而是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进行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实可以不去,但还是去了。这就说明自己立志不坚,行动不能斩钉截铁? “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决心“戒之”。
及至十一月初九日,他上午到陈岱云处给陈母拜寿。饭后本打算回家学习,结果在朋友的劝说下一起到何子贞家去玩,在那里和人下了一局围棋,接着又旁观了一局。在看别人下棋时,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一方面是想放纵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却是不断想起自己对自己许下的种种诺言。终于,一盘观战未了,他战胜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读兑卦”。
曾国藩在日记曾经深入分析过自己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交游往来。他发现,有一些社交活动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另一些,则是可去可不去。问题就出在这些可去可不去的活动他多半都参加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因为想建立“为人周到”、“好交好为”的名声,也就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另一个,则是因为自己性好热闹,在家里坐不住。
分析之后,他下决心缩小社交圈子,改变在朋友中的形象,以节约社交时间用于学习和自修。但因为以前交游太广,不可能一下子切断许多社会关系,所以必须采取渐进方式:“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
征逐之习可渐改,意气之过则须立克。曾国藩修身之始,另一个着力点是改掉自己的暴脾气。
和大多数初入社会的青年一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待人天真,一片直拙。一旦成为朋友,就掏心输肝,同时也要求对方对他毫无保留,缺乏人我相交必需的距离感和分寸感。曾国藩既然以“圣人”自期,也不自觉地以圣人标准要求朋友,经常说话过于直接,不留余地,不分你我,因此很容易与朋友发生冲突。这个缺点,他的一些朋友知之甚深。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陈岱云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他与郑小珊打架一事而发。郑小珊是曾氏的湖南老乡,同为京官,年长曾国藩近十岁。他精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与此与曾国藩往来十分密切,因为一件小事,郑小珊对曾国藩口出“慢言”。曾国藩与这样一个同乡而兼前辈口角起来,破口大骂,并且用语极脏,这无论如何都有应反省之处。
有一次他到陈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当天晚上他这样批评自己:“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做子矣。日日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日记中关于这样的反省实在笔笔皆是。
3 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曾国藩认为,磨练自己要有如鸡孵蛋般的耐心和韧性。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针砭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
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慢,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岁的他写信给弟弟说:
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他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
同治八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
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
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他接人待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他总结说:
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梁启超在盛赞曾国藩的“有恒”时说: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