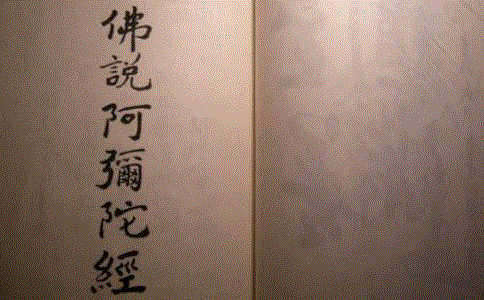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
发布时间:2022-05-15 21:08:52作者:阿弥陀经全文网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
本文考察了胡适禅宗史研究的历程,并详细地评论了他在发掘和整理禅宗新史料、弄清初期禅宗史上的一些重要史实等方面所作的研究工作。从而认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虽有不少主观武断和谬误之处,但从总体上来看,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非信仰者的立场,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今天研究禅宗史也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过去那种一概否定的批判是不公正的。
一.胡适对于禅宗史的研究,是他整个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佛教(主要是禅宗)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曾这样写道:
“中世第二时期。自东晋以后,直至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经典,次第输入中国,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顗、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又说:
“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料,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平心而论,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的。”
同时,胡适也很注意佛教所以能在中国传播的原因,以及佛教在社会风俗、礼仪、伦理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如他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读宋人穆修的文集一事。他对其中一篇题为《蔡州开无寺佛塔记》的文章,十分赞赏,认为他对佛教的流传及其社会作用的评述,有可取之处。他介绍该文的一些观点,同时评论说:
“他的大旨说佛法之行,是因为他能‘本生民甚恶欲之情而导之’,所以‘能鼓动群俗之心如趋号令之齐一’。这是很平允的见解。”
“他说:‘如死生祸福之说,使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亦尝言之,则人亦必从此六圣人而求之。如其圣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则人焉得不从佛氏而求之也?’这是韩愈所讳言的。”
“他又说:‘予谓世有佛氏以来,人不待礼义而然后入于善者,亦多矣(“然”字当行)。佛氏其亦善导于人者矣。呜呼,礼义则不兢,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独盛于时也。’这是很忠恕的估价。”
“又说:‘就其实而言之,则隆塔庙诚佛事之末。苟以时观之,能恢赫显灼,使人见之起恭生敬,则无如塔庙助佛之大。故虽穷远僻阻,川涂所出,必有佛之塔庙以瞻向于俗也。’这也是有历史眼光的话。”(《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2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穆修和胡适对佛教的评价是否正确,然其中透露出胡适对佛教历史的关心则是无疑的。因此,当胡适在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8年)后,即开始着手于佛教禅宗史的研究。
大约自二十年代初至一九三五年,是胡适研究禅宗史的第一时期。他的第一篇有关佛教禅宗的论文,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发表的题为:《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然而在这之前,从现存的他的日记中,我们得知,他在一九二一年九月至十月,曾在中哲史课中讲过佛教①,一九二二年六月间,又曾讲过《佛教略史》和禅宗②。一九二二年三月二日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拟重编《中古哲学史》拟分两部,六篇:
部甲,两汉魏晋
篇一,道家的成立。
篇二,新儒教的成立。
篇三,自然主义的发展。
部乙,六朝唐(印度化的时期)
篇一,输入时期。
篇二,分宗时期。
篇三,革命时期。”③(《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 1985年版)
此外,我们从胡适部分藏书的题跋和眉批中,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一时期曾认真地阅读并研究过一批佛经和禅宗典籍的。如在《维摩诘所说经》④一书封面上,胡适有两段题跋:
“这是一部很荒诞的小说,居然有人奉作经典,岂非怪事!适。九,九,十二。”
“四年前的跋大谬。此书有文学意味,故能行远;说理简单而不繁,故能传久而效大。《法华》与《维摩》真二大魔力,最不可忽。适。十四、一、廿九。”
又,在《达摩禅经》一书封面上,他也有两段题跋:
“此是伪经。适。十三.三.十八。”
“此不是伪经,前记太武断了。此即《修行方便论》,今改称《达摩禅经》,是容易误会的。适。十四.三.三。”
从以上两书的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佛教经典的了解,也在随时发生变化。
又如,在《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一文的末尾,胡适引用了《宗门武库》(宋道谦编)中,晦堂(祖心)向草堂(处元)讲的一个猫捉老鼠的故事,来与他前面引的《修行道地经》中写的一个擎钵大臣的故事进行比较,这两个故事都是讲专心壹志,心不放逸的效用的。关于这个故事,胡适在他读过的《宗门武库》一书中,有简明的眉批:“此是方法论”。在同书中,还有两处的眉批也写着“此是方法论”。可见胡适是很注意禅宗的方法论的。其中有一则为宋代名僧五祖法演讲的贼教儿子独立谋生的方法的故事,很有趣味。胡适特别引用出来,与上述擎钵大臣故事加以对比,以说明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和特点。(详见《中国禅学的发展》讲演稿,日本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

再如,他在唐华严宗大师澄观的《答顺宗心要法门》一文末尾有一重要题跋:“这一篇已是印度系与中国系融化时代的文章了。到宗密的时候,这个趋势更为明显。适。”
一九二七年夏,他校读了《续藏经》本中的《曹溪大师别传》,长短校记约二十余条,出末题跋说:“1927年八月一日校读此传毕。天大热,以校书解暑热。胡适。”一九二九年,他又校读了宗宝本《坛经》,书面里页题跋说:“此本五十四叶,百0七面。唐本比此本约少45面,计少百分之四十二。十八、九、廿六,胡适。”第二年(一九三0年)一月,胡适写成《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一文,就是用了上述两书的校读成果。
诸如此类的读书题跋和眉批尚有不少,这里不能一一列举。然而,仅此也可以看到,胡适为了写好禅宗史,是认真地研读过一批佛典的①。同时,他也注意用西洋哲学作“比较参证的材料”(《中国哲学史大纲绪言》语),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对禅宗史的研究作出了某些新的探索。
一九三0年,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一书的自序中,提到他民国十三年(1924年)试作《中国禅学史稿》一事,并说已写到神会,因疑点重重而不得不搁笔(此事在他晚年的口述自传也提到过)。关于此稿的详细内容,现在已无从知晓。但可以推断,上面提到的《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以及一九二七年发表的《菩提达摩考》,一九二八年发表的《禅学古史考》等论文,都可能是《史稿》内容的一部分。
一九二六年,胡适在伦敦、巴黎发现敦煌卷子中神会等人的重要资料后,即准备“改作”他的《史稿》。这在他一九二八年给汤用彤的信中可以看到。他说:“我的禅宗史稿本尚未写定,大部分须改作,拟于今夏稍凉时动手改作。”(《胡适文存》第三集卷四)遗憾的是,他的这部禅宗史始终也没有能写定出版。不过,其基本内容大概在答汤用彤书中所列的十三条大纲,以及一九三二年他用英文发表的论文:《Development of the Zen Buddhism in China》(《禅宗在中国的发展》),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中古思想小史》讲课提纲,一九三四年在北师大所作的题为《中国禅学的发展》的四次演讲中,都已包括了。
再者,他在一九二八年发表了《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一九三0年发表了《跋曹溪大师别传(坛经考之一)》和《荷泽大师神会传》,一九三一年发表了《楞伽师资记序》,一九三四年发表了《跋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藏北宋惠昕本坛经影印本(坛经考之二)》,一九三五年发表了《楞伽宗考》等等,这些也都是他在获得敦煌写本和日本发现的新史料后,为改写他的禅宗史所作的整理、研究工作。
在这之后,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中断了十七年之久。一九五二年,他先后撰写了《朱子论禅家的方法》和《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又重新开始了他的禅宗史研究课题。由此至一九六二年逝世止,是他研究禅宗史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他运用新发现的敦煌写本资料,对《神会和尚遗集》作了校订和补遗,又根据各种历史文献、碑铭等资料,写成了不少关于初期禅宗史的论文。据粗略的统计,在这十年中,他写成有关禅宗史的论文,大大小小约有四十余篇。其中除小部分在他生前公开发表外,绝大部分都是手稿②。胡适这一时期禅宗史的研究,仍以史料考证为主,继续对他第一期研究结果进行补充、加深或修正。其中有不少敏锐和精到的看法,然在基本观点上则与第一期没有什么改变。如一九五三年,他在蔡元培八十四岁诞辰纪念会上作了一个题为《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的讲演,其基本的观点和内容,与他十九年前在北师大的讲演,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可说是前后一贯了。
二.胡适对于禅宗史的研究,可说是围绕着以神会为中心而展开的初期禅宗史的研究,其中尤以史料考证为主。关于胡适禅宗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我认为国内学术界尚缺乏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五十年代中期,开展了“胡适思想批判”的运动,那时,对许多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评价,采取了简单的一概否定的非科学态度。对于他在禅宗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和方法,同样也不加分析地一概予以否定,这是很不公正,很不实事求是的。
胡适在初期禅宗史的研究中,确实有不少以偏概全,主观武断之处,如断言《坛经》作者为神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非信仰者的立场,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人①。他的研究成果,对搞清楚初期禅宗史上的许多史实,是有重要意义的。下面我想具体讨论一下胡适在初期禅宗史研究中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及其评价。
(一) 禅宗新史料的发掘
长期以来,人们按照宋以后编写的各种禅宗灯史来了解和研究禅宗发展的历史,习闻于五祖弘忍以袈裟为凭,秘密传法与六祖慧能,以后慧能下分两系(南岳青原),再传而成五家(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至宋临济又分杨歧、黄龙两派,遂成所谓五家七宗的传灯谱系。胡适在研究禅宗史的过程中,撰写至慧能、神会而发现初期禅宗史上的种种疑问,于是不得不搁笔而转向对于初期禅宗史料的考证和探索。他首先注意到从新发现的大批敦煌唐写本中去寻找后代佚失的禅宗史料。
一九二六年,他在伦敦、巴黎两处所藏的敦煌唐写本中,发现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初期禅宗史料。其中最重要的有《神会语录》、神会作的《顿悟无生般若讼》(即《显宗记》)、《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以及净觉的《楞伽师资记》等。一九二七年四月,胡适回国时路过东京,与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常盘大定、矢吹庆辉等会晤,又得知矢吹庆辉从伦敦影得敦煌本《坛经》。一九三0年,胡适将发现的神会资料编集在一起校订出版,题为《神会和尚遗集》。《楞伽师资记》则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由朝鲜学者金九经整理出版。
这些初期禅宗史资料的发现和出版,引起了日本研究中国禅宗史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先是,一九二七年八月,胡适在伦敦《泰晤斯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禅论文集》的书评,其中指出铃木没有注意到敦煌资料的问题。这件事对铃木启发很大。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一九二七年,胡适批判笔者在伦敦出版《禅论文集》第一集的书评刊登在当时《泰晤斯报》的副刊《周刊文学》。因为当时对敦煌发掘的禅资料,毫无所闻,所以认为唐土禅宗初期的历史观仅止于传来者。同时,想到在当时能作如此批评的人,在英国尚无二人,笔者感到惊讶。于是决心查看敦煌出土的资料。”(转引自柳田圣山的《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见该氏编《胡适禅学案》)
同时,胡适还关注于保存在日本的古代禅宗史料,发掘出了《曹溪大师别传》,并据此写出了《坛经考之一》,对查清《坛经》演变史,有着重要的价值。之后,日本又发现了另一种敦煌本《神会语录》(石井光雄影印本),发现了京都堀川兴圣寺本《坛经》(惠昕本)等,于是,铃木大拙据兴圣寺本校订了敦煌本《坛经》,用胡适本校订了石井本《神会语录》,又单独地校订了兴圣寺本《坛经》等,于一九三五年正式出版。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又陆续发掘和整理出版了不少禅宗的新史料。这都给初期禅宗史研究的深入和开辟新的局面,提供了史料上的充分条件。追根溯源,胡适在发掘禅宗新史料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杀的①。
(二) 神会和尚历史地位的发现
按照传统禅宗灯史的记载,神会和尚只不过是慧能晚年的一个小徒弟,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地位。胡适根据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以及《略疏钞》)、《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所载的神会传记,以及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资料,撰写了《荷泽大师神会传》。在传的结尾处,胡适这样写道:“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
在这一大段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赞词中,有不少过誉和武断之处。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遭到禅宗史研究者的非议。不过,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认胡适发现的神会在确立禅宗(南宗)历史地位上的重大作用,对于研究初期禅宗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通过胡适对神会的研究,揭示出了初期禅宗发展史上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诸如:
1.慧能在世时,至多只是南方的一位一方宗师,而当时的北宗领袖神秀,却曾身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不仅如此,又据宗密言:“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指神秀等)渐门炽盛于秦洛。”(《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下)这就是说,在慧能生前和死后二十年间,北宗渐修法门在社会上的势力和影响大大超过南宗。其时,神秀的大弟子普寂还曾自称七祖,尊神秀为六祖。而慧能在禅宗中的地位并不高。这些史实是历代禅宗灯史所讳言的,并编造出各式各样的伪史来歪曲这一历史事实。
2.慧能的顿悟法门是经过神会的大力宣传,凡至通过拼却身命的多次公开辩论(今存《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是当时辩论会的实录),才逐渐地为广大僧俗所接受,从而确立起他的社会地位的。在这些辩论中,神会对神秀、普寂一系的师承和渐修法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和斗争。他指斥神秀门下“师承是傍,法门是渐”,甚至公开宣称当时“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为不可思议”的普寂禅师的教门,“与南宗(此‘南宗’指菩提达摩所传之禅学)有别”,也就是说,神秀、普寂一系所传法门是违背了菩提达摩的原旨的。同时,他却声称:“我六代大师(自达摩至慧能),……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以上均见《南宗定是非论》)这也就是说,只有慧能的顿悟法门才是菩提达摩以来的根本宗旨。其实,这完全是神会为了争法统而编造出来的。事实上是,神秀、普寂一系倒是承继了达摩以来的基本禅法的,而慧能、神会则是改造了达摩以来的禅法。神会为争法统,得罪了当时尚有显赫地位的神秀、普寂一系,因此一度曾遭到迫害。以后,神会借度僧资助军饷立功,受到肃宗皇帝的供养,于是神会“敷演显发能祖之宗风,使秀之门寂寞矣。”(见《宋高僧传》本传)宗密在《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说:“德宗皇帝贞元十二年(796),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神会)为第七祖。内神龙寺见有碑记。又御制七代祖师赞文,见行于世。”贞元十二年时,宗密已十六岁,想必宗密曾亲闻此事,亲见神龙寺碑。可见,经过神会的奋斗,慧能的顿悟法门及其师承,甚至得到了官方帝王的确认②。当然,慧能提倡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得以在当时社会上受到承认,并在以后历史上发生深远影响,是有多方面的社会的和理论的原因,非神会一人之力所能达到的。但是,神会在禅宗南宗历史地位的确立上,确是一位功臣,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3.胡适断言神会为《坛经》(敦煌本,下同)的作者,不免失之武断。而且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所谓“内证”,也未免失之偏面,即只采取神会语录中与《坛经》思想相符者,至于两者之间的差异①,则只字未提。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神会及其一系与《坛经》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神会的思想与《坛经》的思想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坛经》中的顿悟法门也是经过神会大力倡导后,才为社会承认和发生重大影响的。其次,据韦处厚的《兴福寺大义禅师碑铭》说,神会的弟子门“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全唐文》卷七一五)胡适解释此文说:这里“明说《坛经》是神会门下的‘习徒’所作”。(《神会传》)这完全是胡适对韦文的误会和曲解。然而,这段记述却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坛经》作为传法宗经,是从神会一系开始的。我们甚且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坛经》之所以名“经”,很可能也是由此而来的。(《坛经》原来很可能也像《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那样,称为《曹溪大师……坛语》,由于神会弟子们以此传法,尊为宗经,然后才改称《坛经》的)。同时再推测《坛经》一书最初是由神会及其弟子们整理或修订而成的,也就不为无据了。
4.对于初期禅宗思想演变的轨迹,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胡适研究了达摩以来禅法的主要思想,对神秀普寂和慧能、神会,所谓北宗和南宗的思想也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印度禅和中国禅之间的不同。慧能、神会一系南宗,其实是以中国禅去改革和取代印度禅。同时,他还指出,在神会的思想中,有明显的将佛教因果理论与道家自然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神会屡屡强调的不假修习,“莫作意”等,都是“自然主义的无为哲学”。这些分析不仅有助于把握神会思想的特点,而且对了解整个禅宗(南宗)思想的特点以及其发展趋向,都是有启发的。
(三)《坛经》演变史的考察
自敦煌本《坛经》重新问世后,人们发现原传世的宋元明本《坛经》在内容上与敦煌本有很大的不同。在文字上也逐渐加多至一倍左右。三十年代初,日本发现经晚唐僧惠昕整理过的《坛经》(称兴圣寺本),其内容虽与敦煌本小有不同,但基本一致,可据以与敦煌本进行互校,弄清古本《坛经》的原貌(胡适的《坛经考之二》,就是考证兴圣寺本的)。以现存各种《坛经》本与敦煌本相比较,可以发现,最早发生内容上重大变化的当为北宋初著名的“辅教大师”契嵩的改编本。契嵩自称得到“曹溪古本”,并据以校改俗本。其后的元宗宝本,只是在契嵩本的基础上添枝加叶而已。因此,关键是要考察清楚契嵩改编本所依据的“曹溪古本”。胡适最先注意到了久已在中国失传,而在日本尚有传本的《曹溪大师别传》一书。此书在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带回的经目中已有(题作《曹溪大师传》一卷)。又根据本书内传法悬记:“吾灭后七十年”,以及“大师……先天二年壬子岁灭度,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云云,此书大约作于慧能死后七十年左右,即建中二年(781年)左右。经过胡适的详细考证,可以确认,契嵩所谓的“曹溪古本”,其实就是这本《曹溪大师别传》。因为契嵩改编的《坛经》中所增加的主要内容,都见存于《曹溪大师别传》。从某种意义上讲,契嵩的改编本,可以说是敦煌本(或惠昕本)与《曹溪大师别传》的合编本。这样一来,《坛经》内容上演变的秘密就被揭开了,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工作。但是,胡适当时仅注意于一些具体史实方面的考证,而对《曹溪大师别传》的思想内容、方法则未加全面的深入考察,以至认为《曹溪大师别传》“是一个无识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不幸契嵩上了他的当。”(《坛经考之一》)这个结论是需要重新加以考察的②。
(四)关于“楞伽宗”的考察
这是关于相传禅宗北宗师承的考察。胡适根据道宣的《续高僧传》、敦煌写本中发现的净觉撰《楞伽师资记》等资料,认为:“楞伽宗自成一派”,“楞伽宗即是后世所谓‘北宗’,神秀一支尚是此宗正统。后起之‘南宗’乃是一支革命军,虽自附于达摩,实不是楞伽宗。”(《胡适致金九经书》,附见《姜园丛书》校刊《唐写本<椤伽师资记>》)一九三五年,他又发表了《楞伽宗考》,详细地考证了“楞伽宗”的传承和宗旨,最后得出四点结论:1.袈裟传法说完全是神会捏造出来的假历史;2.神秀与慧能同做过弘忍的弟子,当日既无袈裟传法的事,也没有“旁”、“嫡”的分别。“师承是傍”的口号,不过是争法统时一种方便而有力的武器;3.渐修是楞伽宗的本义,这一宗本来“法门是渐”。顿悟不是楞伽的教义,他的来源别有所在;4.从达摩以至神秀,都是正统的楞伽宗。慧能虽然到过弘忍的门下,他的教义——如果《坛经》所述是可信的话,已不是那“渐净非顿”的楞伽宗旨了。至于神会的思想,完全提倡“顿悟”,完全不是楞伽宗的本义。最后他还说:“可知神会很大胆的全把《金刚经》来替代了《楞伽经》。楞伽宗的法统是推翻了,楞伽宗的‘心要’也掉换了。所以慧能神会的革命,不是南宗革了北宗的命,其实是一个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
胡适的这番考察和论断,和他关于神会的研究一样,有许多过分夸大和主观武断之处。因此,不少佛教史或禅宗史的研究者,不同意他关于历史上曾存在过“楞伽宗”,以及所谓“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之类的论断。这些问题确实可商榷。不过,如果把胡适那些带有文学色彩的描绘和夸张排除掉,他所考证的关于自菩提达摩以来,从南北朝至唐,有一大批依《楞伽经》义习禅、宣教的“楞伽师”,神秀一系的渐修法门主要是继承了楞伽师的传统禅法,以及楞伽师禅法的特点等,都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对研究初期禅宗的理论演变过程,也是有启迪的。因此,他的《楞伽宗考》发表后,对中日两国的禅宗史研究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日本著名禅宗史学者柳田圣山在《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胡适斩钉截铁的武断,强调此说(指“楞伽宗”),影响了一九三五年以后,中日两国初期禅宗史的研究工作,没有人能脱出他的断定。譬如从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昭和十四年[1939])开始,接着有铃木大拙的《禅宗思想史研究第二》(昭和二十六年[1951]),以及关口真大的《达摩大师之研究》(昭和三十二年[1957]),都被胡适《楞伽宗考》的荫影笼罩着。”(见该氏编《胡适禅学案》)
(五)此外,胡适还有不少细密的考证,也不乏精到之处,它对于推进禅宗史的研究,也甚有助益。此处略举二例,以示一斑。
1. 如胡适从裴休撰宗密碑(作于唐大中七年,853年)中发现,在叙述传法世系中有:“能传会为荷泽宗,荷泽于宗为七祖。又传让(怀让),让传马(马祖)。马于其法为江西宗。”怀让是相传的“南岳”一系。于是,胡适指出,“此碑不提及所谓‘青原行思’一派。”(《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见《胡适禅学案》)同时,他又在贾餗撰灵坦碑(作于唐宝历元年,825年)中也发现文中有:“曹溪既没,其嗣法者,神会、怀让又析为二宗。”其中也不及“青原行思”一派。因此,胡适断言:“石头希迁一支更后起。所谓,‘青原行思’可能也只是‘攀龙附凤’的运动里的一种方便法门而已。”(《致柳田圣山书》,同上)这一发现和考证,对研究传统灯史中关于慧能后传为南岳、青原两系之说的形成和演变历史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胡适在考证中一再指出,在某宗派盛行时就会出现“攀龙附凤”的现象,如他指出牛头法融的攀附北宗,宗密与马祖道一等之攀附南宗等。他经过考证,宗密实出于成都净众寺无相(金和尚)门下的神会,但他却故意把他混同于东京荷泽寺的神会。胡适的这些考证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用更充分的史料予以验证,但他指出这种历史现象,是值得禅宗史研究者予以充分注意的。
2. 又如,他从大历七年(772年)独孤及所作《舒州山谷寺三祖镜智(僧粲)禅师碑》中发现有这样的话:“弘忍传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秀公传普寂,寂公之门徒万,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庑,龙象又倍焉。”(《文苑英华》卷八六四)据胡适考证神会死于宝应元年(762年),至大历七年才十四年①。于是胡适指出:“在大历初期,北宗普寂门下的弘正一支势力还很大,还有压抑能大师一支的企图。”(《致柳田圣山书》)再有,他根据白居易的《传法堂碑》中所说的“自四祖以降,虽嗣正法有冢嫡,而支派者犹大宗小宗焉”;以及贾餗灵坦碑中所说的:“代袭为祖,派别为宗”等,指出这些说法“都代表元和年间的各宗派和平共存的容忍气氛。”(同上)他还分析了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中修正和曲解神会的顿悟说一事,指出此时由于激烈的斗争已过,于是就出现了宗密这样的调和论主张。胡适的这些见解,为禅宗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胡适的禅宗史研究工作,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即以其第二期的研究工作来说,也已过去三十年左右了。然而对于他在禅宗史研究中的成绩和缺点,我们都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当年,他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术界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直至今日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一九七四年,日本著名禅宗史学者柳田圣山主编了《胡适禅学案》一书,收集了胡适有关禅宗史研究的论文、讲演、手稿和书简等三十余篇,为研究胡适禅宗史研究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柳田圣山先生还特意撰写了一篇《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的长文,全面地回顾和论述了胡适禅宗史研究工作的过程,以及其影响和意义,特别介绍了在日本的中国禅宗史研究者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在此文的结尾,柳田先生说:“时至今日,对中国禅学作研讨的人,在相当期间还不能忽视胡适的遗业。”我认为,柳田先生的这评价是很平允的。对于中国初期禅宗史的研究,我们不应忽视胡适已取得的成果,而应当在此基础上前进和深入。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它在我国文化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禅宗史的研究工作十分薄弱和落后,至今也还没有能够编写出一部禅宗史的专著来,说来实在令人惭愧。如果通过对胡适禅宗史研究工作的回顾和评论,能使我们在他工作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一步,这也可说是我撰写这篇“平议”的愿望之一。
--------------------------------------------------------------------------------
* 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① 《胡适的日记》:“十、九、廿八(W)上课,……中哲史讲佛教第一时期。”(第230页)“十、九、廿九(Th)上课,中哲史讲佛教第一时期至第二时期。”(第231页)“十、十、五(W)上课,……中哲史讲佛教第二时期。”(第235页)“十、十、六(Th)中哲史讲[佛教]第三时期完。”(第26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胡适的日记》:“十一、六、二(F)上午,上课,讲佛教略史。”(第336页)“十一、六、九(F )七时上课,……中古史讲小乘各宗。”(第375页)“十一、六、十七(Sat)上课,讲大乘的坠落方面。”(第382页)“十一、六、廿三(F)上课,……中古折学讲禅宗,作一结束。”(第38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 据现存胡适《中古思想小史》手稿(1931年至1932年在北京大学讲课时用)看,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设想编写的。其中佛教部分计五讲:“第八讲,佛教(介绍佛教产生及其基本情况)。第九讲:佛教的输入时期。第十讲:佛教在中国的演变。第十一讲:印度佛教变为中国禅学。第十二讲:禅学的最后期。”(台湾胡适纪念馆刊印胡适手稿本《中国中古思想小史》)
④本文所引原胡适藏书,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①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胡适的日记》1922年6月1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读Farguhar’s《 Outline of Rel. Lit. in India 》,仍未完。此书甚好,其中论《法华经》一节甚有理。我前年认《五百弟子受记品》以下为后人增入的,遂不大注意他们。Farguhar指出21至26为第三世纪增入的,但他又指此诸篇可见:(1)陀罗尼(咒)之信仰,(2)观世音之信仰,(3)极端的修行,如焚指焚身(《药王品》)之信仰。此皆我所不能看出的。”(中华书局版,第379-380页)
② 这些手稿均已收入“胡适纪念馆”刊印的《胡适手稿》第七至十集中(1970年台湾出版)。
① 胡适对宗教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佛教也不例外。直至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还激烈地批评道:“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钜。”“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因此,他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他还说,他的禅宗史的研究工作,就是做一种“耙粪工作”,即把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见胡适英文口述稿,唐德刚编校译注《胡适的自传》)
又,胡适在1934年北师大的讲演中说:“从前许多大师,对于禅宗的材料,都爱作假。所以经我揭穿之后,有许多人不高兴。不过我不是宗教家,我只能拿历史的眼光,用研究学术的态度,来讲老实话。”一九六一年在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的信中,也说:“先生似是一位佛教徒,似是一位禅宗信徒,而我是一个中国思想史的‘学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所以我与先生的根本见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致。”(见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胡适与日本著名禅宗史学者铃木大拙也有同样的分歧和争议。
① 直至晚年,胡适仍极关心禅宗史料的发掘工作。一九五八年他发表了《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一九六O年又发表了《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议(刘澄集)>》等,并根据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再进行一次“大索”,以期发现更多的流传于日本的古禅宗史料。同样的建议也详见于《An Appeal for a systematic search in Japan for Long-Hidden Tang Dgnasty Source-Materials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Een Buddhism》(1960年,见《胡适禅学案》)。
② 一九八三年,在洛阳龙门西山唐宝应寺遗址出土了神会的身塔碑。此碑由其徒慧空撰,法璘书,立于唐永泰元年(765),即神会死后七年。此碑额全文作《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腹建身塔铭并序》。由此可见,在其徒众中,早已称神会为“第七祖”了。(碑文见《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① 神会语录和《坛经》(敦煌本)中的某些差异是存在的。如神会语录中多处征引《涅槃经》论佛性问题,而在敦煌本《坛经》中则完全没有这一类的论述。
② 《曹溪大师别传》一书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是了解禅宗思想全貌的十分重要的原始资料。该传中突出地论述了涅槃佛性理论,正是禅宗“见性成佛”的根本理论依据。然而这在敦煌本《坛经》中却是见不到的。欲知其详请参阅作者的另一篇论文:《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别传>、以及初期禅宗思想》。
① 据一九八三年出土的神会身塔碑记载,神会死于乾元元年(758年)至大历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