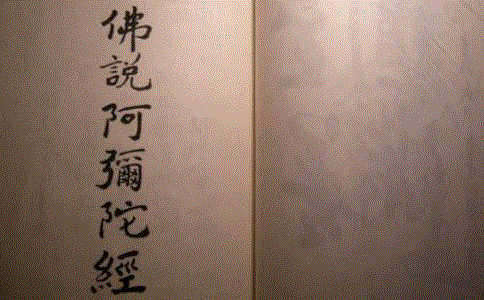也谈汉文佛教大藏经的系统问题
发布时间:2022-05-06 11:10:41作者:阿弥陀经全文网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写的文章里,我把汉文佛教大藏经刻印的历史,依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大体分为四个时期,即:北宋时代的官版大藏经及其覆刻藏;两宋之际及南宋灭亡前后以寺院为中心的私刻藏经;明清时代的官版藏经及近代以来的铅印本大藏经和影印本大藏经。应该说,这四个时期的划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时代背景方面的某些特点,比如北宋末年至南宋灭亡前后的这一历史时期,我国汉族统治者在中国北方的统治从根本上动摇了,作为宋王朝的中央政权已无力也无暇顾及以官修的形式组织大藏经的雕印,所以这一时期所刻藏经几乎全部是由民间集资,并且是在中国的南方刻造的;同时,以寺院为中心,由僧人主持刻藏也是这一时期刻藏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然而,这种时期的划分并没有涉及各版大藏经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四个时期的划分只反映了大藏经雕刻史上,因时代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大藏经雕刻时的一种历史状况,几乎不涉及大藏经的内容。那么,各版大藏经之间在内容方面有没有关系,这种关系如何,有没有不同的系统?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去年,在《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上发表了上海师范大学徐时仪教授的文章《金藏、髙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渊源考》,就以十分明确的观点和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论述了这一问题。徐教授通过唐玄应撰《一切经音义》收录于不同大藏经中的两个版本的考察,提出汉文佛教大藏经在这里至少可以区分出高丽藏系和碛砂藏系两个系统。徐教授的这种考察是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指出:收录于丽藏系的《一切经音义》释经458部,而碛砂藏系的《一切经音义》释经440部。其中碛砂藏经缺的丽藏系卷5所释《超日明三昧经》等21部经,又于卷13多出《八师经》等数部经;就所释词语说,二者也有显着的不同,丽藏系有而碛砂藏系无的词语为212条,碛砂藏系有而丽藏系无的词语为214条;就所释同一词语的释文亦多有不同等(徐教授的论证十分精细,我这里只是例举,难尽其意)。作者根据上述的考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丽藏.金藏.碛砂藏和永乐南藏本等藏经大致可分为丽藏和碛砂藏两个系列,二者的不同在于所依据的传写本不同。[1]” 徐教授的这种研究是对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的一种深化,是为推动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
二至清《龙藏》我国历代汉文大藏经的类别
汉文佛教大藏经是在中国佛教这个大环境下形成的,它们的渊源和流传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隋及初唐时代形成的官写本“一切经”是它们共同的源头,而中唐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则标志着汉文佛教大藏经编辑体例的最终形成。宋初中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就是据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在四川成都流行的一种官写本大藏经雕造的。之后,自北宋至清乾隆初年(约971-1739)的近800年间,我国的刻本大藏经代有新出。粗略统计现有印本发现的大约有16种,它们是《开宝藏》、《契丹藏》、《赵城藏》、《崇宁藏》、《毘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元官版藏经》、《元延佑本大藏》、《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和清《龙藏》等。
中国历代大藏经就其收经内容说,应该说是大同小异的。所谓大同,即这16种大藏经收录经籍的基本部分,大体是《开元录·入藏录》所收录的1076部5048卷的内容,这是诸大藏版本所共有的;其次,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至宋真宗咸平二年(982-999)间由天息灾、施护、法灭等翻译的北宋新译经30帙约187部279卷,也几乎是历代大藏经共收的内容。这两者相加已有1263部5327卷,已约占各藏收录经籍内容的4/5。另据日本学者小野玄妙所着《佛教经典总论》中“刊本大藏经总览”[2],其所列14种藏经(含个别经录)对照表,可清楚地看到,在所录1444种典籍中只有34种中国着述不为各藏共收,而共同的内容多达1410部。中国清以前的历代大藏经所收经籍部数,如果不包括《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是以清《龙藏》收录经籍最多,为1669部。
下附历代大藏经收经部卷数一览表。(略)
如果拿清《龙藏》的1669部与1410部相比,两者相差仅只259部,不到全藏的1/6,这就是大同小异。小异的部分一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唐以前遗漏未编也包括个别北宋时期的译经;另一部分则是历代的中国着述,这是主要的部分。比如《契丹藏》,其基本的内容是《开元录·入藏录》的5048卷,后来又增补了北宋的新译经30帙,这是与《开宝藏》相同的地方。但《契丹藏》因受《续一切经音义》及《续贞元录》的影响,它所收录的40卷《新大方广佛教华严经》,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药事》等7种律典。《护法沙门法琳传》等就成为《契丹藏》与《开宝藏》相区别的内容。又如《崇宁藏》、《毘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等。它们自“天”帙《大般若经》始至“毂”帙《护国经》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它们的共同处。但之后则出现了不同,比如《普宁藏》、《碛砂藏》在之后增加了28函秘密经;碛砂藏增加了《传法正宗记》等5部,《普宁藏》则增加了《白云和尚初学记》等8部,从而反映了各自的特点。
尽管如此,在近800年的雕刊史上,我国清以前的历代大藏经又因为流行地区、所据底本及时代的不同等各种原因,形成了比较接近的几种类型,也就是如徐教授所说的系统。这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来归纳这些类型,这些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其特点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这里,我依据学术界都熟知的一些资料,提出我国历代大藏经大致有四种类型的看法,不知当否,请诸位指正。
第一种类型就是以《开宝藏》为代表的版本。这是北宋初年以流传于益州(成都)的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为底本雕造的一部官版大藏经。但这部大藏经对《开元录·入藏录》已作了某些改动,主要是对个别经的分卷作了调整,并创新了一种23行14字的版式。这种版本的延续就是它的覆刻藏《赵城藏》和《高丽藏》。
第二种类型是《契丹藏》为代表的版本。我们通过对山西应县发现的《契丹藏》印本及《房山石经》辽金刻部分的研究,可清楚地得知《契丹藏》的基本部分完全是依据《开元录·入藏录》雕造的,不论是收经的内容,还是排列的顺次及帙数,都与《开元录·入藏录》相吻合。这种版本还继承了我国唐及唐以前写本大藏经的传统版式,即每纸28行每行17字的版式[3]。这种版本的延续只有《房山石经》的辽金刻部分。
以上两种版本都是以卷轴装面世,反映了较古老的一种版本。
第三种类型是以《崇宁藏》为代表的版本。应该说,这是历代大藏经中影响面最大的一种版本,自《崇宁藏》始,之后的《毘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以及明初的《初刻南藏》等都是这种版式本的延续。它们在版式上开创了一种被称作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大多数每版折成5个半页,每半页6行共30行,每行17字;在收经内容及千字文编次上几乎与《开元释教录略出》一致。
第四种类型是以《永乐南藏》为代表的版本。这是在编排上大胆突破《开元录·入藏录》体系的一种大藏经版本。它将《开元录·入藏录》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的排列顺序,改变为大乘经、小乘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这种分类及排序上的改变,将之前各版式大藏经相差不多的经籍排序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改变了大藏经的结构。这种版本直接影响了之后的《永乐北藏》、《嘉兴藏》及清《龙藏》,使之成为一种体系。现将这四种类型的大藏经版本的情况举例列表如下:(略)
上列这份表格想说明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① 尽管各版大藏经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时代雕造的大藏经版本中确实存在着差异和彼此相近的体系。从对比中可以看出,由《指要录》反映的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4]与之后的《赵城藏》所收经籍的分卷与千字文帙号完全一致;《开元释教录略出》与《崇宁藏》的经籍的分卷及千字文帙号又几乎全同;而《永乐南藏》与《清藏》大多数经籍的分卷与千字文帙号也基本相同,而这几组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② 这种体系的存在,与某种经录有着一定的关系。据《指要录》,《开宝藏》“若通前计大小乘经律论,总五千四十余卷四百八十帙,以开元释教录为准”[5]。如前所述《开宝藏》所依据的这种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的写本大藏经已对《开元录·入藏录》作了若干变动,如表中所列近20种经籍的分卷发生了变动。
以《崇宁藏》为代表的系统则与《开元释教录略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几乎可以说它的前479帙 (天——群)就是据《略出》雕造的,因而它的第480帙“英”就特别的收录了《开元录略出》;而以明《永乐南藏》为代表的明清诸藏,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改变了《开元录·入藏录》的经籍的排序。这种改变可以肯定地说是受到元《至元录》的影响,尽管明清诸藏并没有完全照搬《至元录》。
③ 《房山石经》因为只刻了1000余部,以大乘经为主,《开元录·入藏录》中除四阿含的小乘经律论及中国着述基本上没有刻,故上列石经栏内有许多空白,但就所刻部分已明显地看出《房山石经》与《开元录·入藏录》的相似关系。
上述这四种体系的大藏经,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比如第一种类型,这是以中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为代表的类型。《开宝藏》曾先后多次传到高丽,高丽王朝据之雕印了《高丽藏》。《高丽藏》的版式及前480帙的内容几乎与《开宝藏》一致,这就表明它们之间有一种较紧密的关系。金朝天眷至大定年间(约1139-1172),在晋南(今运城地区)的解州天宁寺,由崔法珍断臂化缘,用30年左右的时间雕造完成的,发现于赵城广胜寺的《越城金藏》,现经研究发现,它完全是《开宝藏》全藏的覆刻藏。《赵城藏》收经内容及版式与《开宝藏》完全一致,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了它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使它们成为关系较为紧密的一种体系。
《开宝藏》是中国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吕澂先生曾称它是之后历代大藏的蓝本[6]。但事实是除了《高丽藏》、《赵城藏》外,自《契丹藏》始,历代刻本大藏经并没有遵循《开宝藏》的范例。
《契丹藏》是辽王朝主持刻造的官版大藏经。这部大藏经为什么更具传统色彩,成为唐代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的翻刻,我以为有这样两个因素值得注意:
① 主持《契丹藏》雕造的无碍大师诠晓,是在《开元释教录》“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的基础上,增补了“自《开元录》后,相继翻传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也就是辽希麟所撰《续一切经音义》的内容[7],形成了《契丹藏》的主体部分。因此,《开元录·入藏录》的5048卷是《契丹藏》的基础。
② 在唐开元末年,《开元录》的作者智升奉敕亲自将一部官写本大藏经送到“幽府范阳府为石经本”[8]。这部由智升送来的官写本大藏经无疑是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这部官写本大藏经在幽州地区的流传,为200余年后的《契丹藏》的雕造提供了底本,使《契丹藏》成为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唐代官写本大藏经的再现。
上述两点是否是《契丹藏》成为唐代官写本大藏经翻刻的原因,我个人的看法是肯定的。正因为如此,使《契丹藏》、《房山石经》辽金刻部分与《开元录·入藏录》形成了较密切的关系。
《崇宁藏》开雕于北宋神宗年间(约1080),其雕造地是福建福州的东禅等觉院。在如此边远的地区,远离中央政治中心,有条件或敢于以私版的形式雕造新版大藏经,必有其特殊的原因。我认为,如方广锠教授在其着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引《全唐文》825卷所录黄瑫撰《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及《丈六金身碑》的材料就非常重要[9]。
唐朝末年,光州固始人王潮封福州观察,卒后其弟王审知代之,并以“征伐有功”被唐昭宗进封为琅琊王,至五代又被梁朝封为闽王,遂成为福建地方政权的世袭统治者[10]。在王审知统治福建期间,为粉饰其政权,多处造塔并写大藏经藏之。这就是黄瑫碑论中记载的内容之一。
《丈六金身碑》云:
“我公为邦则忠孝于君亲,……牧人则父母于生民。造塔四,其一曰寿山,……其二曰报恩多宝定光,……其三其四曰大中神光,为军旅也,为人民也。缮经五藏,其二进于上,其三会于寿山、定光”[11]。
这些写本藏经,在《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中记载得更为具体,其云:
“我威武军节度使相府琅琊王王公祀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诚,发大誓愿,于开元之寺建塔,建号寿山,仍辅以经藏。……其三年甲子,以大孝之诚,发大誓愿,于兹九仙山造塔,建号定光,仍辅以经藏。……其经也,帙十卷于一函,凡五百四十有一函,总五千四十有八卷,皆极剡藤之精,书工之妙,金轴锦带,以为之饰。天佑二年乙丑,……大陈法令,以藏其经,缁徒累千……[12]。
王审知在开元寺,在九仙山建塔,并以最精美的书工缮写大藏经藏之。这种由地方政权组织缮写的大藏经必是一种官写本大藏经,必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保护;同时,它的内容是5048卷541函,又可以肯定它是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从我们今天研究的角度看,唐末五代时在福州流传的这种备受关注的官写本大藏经,必是宋代在福州雕造《崇宁藏》时的底本。这种官写本大藏经所依据的目录,已不是完全意义的《开元录·入藏录》,而是加了千字文帙号,在内容方面也略有改动的《开元释教录略出》。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由地方统治者组织缮写的官写本大藏经的存在,以及在唐末五代时在闽地的流传,才有了北宋神宗年间《崇宁藏》在福州的雕造。可以想像,没有这种写本大藏经的存在,福州地方的官绅及东禅等觉院的僧人们是不可能雕造出一部《崇宁藏》的。
《崇宁藏》开刻之时,《开宝藏》已经经过两次增补,增补了北宋新译经、唐以前末入藏经及神宗熙宁六年(1073)前敕准入藏的经籍144帙,但这些情况并没有在《崇宁藏》中得到反映,说明《崇宁藏》与《开宝藏》没有关系,完全是另起炉灶。福州东禅等觉院另起炉灶,刻了一部与《开宝藏》不同的新版大藏经,而且还要在基本刻成之后上奏朝廷以求正名,宋徽宗赐名曰“《崇宁万寿大藏》”。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福州地方流传着一部以《开元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这是福建地方的骄傲。这一点很重要,它还可以对为什么同是福州的另一所寺院开元寺,在同一时期又相继刻了另一部大藏《毘卢藏》,而且在内容上又与《崇宁藏》完全一致作出解释。
《毘卢藏》开刻于《崇宁藏》基本完成的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以开元寺的地位及影响,开元寺僧及供养他们的居士大德绝不会把《崇宁藏》印本拿过来重雕覆刻。那么,这两部藏经为什么会在内容上十分的近似?这是因为他们同时都拥有在闽地流传的官写本大藏经。上引黄瑫的碑记中已记载,开元寺本身就有这种官写本大藏经。另据《重簒福州通志》“寺观、福州府、闽县”开元寺一节记载,王审知缮写大藏的地点似乎就在开元寺[13]。既然开元寺有如此优势的地位,他们何以能忍下东禅等觉院抢先据此官写本大藏经雕造木刻本大藏经呢?故在《崇宁藏》雕刻的同时,开元寺就开始筹划并在随后刻了《毘卢藏》。因为所据的底本一样,故其内容也基本一致。
《崇宁藏》、《毘卢藏》之后的南宋期间及宋元之际,在中国南方的江浙地区又相继刻造了《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等诸版大藏经。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明确记载它们之间关系的史料,但从诸版藏经内容的事实出发,可证明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都是以《崇宁藏》为代表的以《开元释教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同一类型的大藏经版本。
历史发展到明朝初年,在朱元璋洪武年间就曾有刻藏的准备,所谓“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14],直到建文时代终于有了《初刻南藏》的问世。但这部大藏经与《碛砂藏》有着密切的关系,仍属于以《崇宁藏》为代表的系列。到了永乐年间,在南京雕造了一部官版大藏经《永乐南藏》。这部大藏经酝酿于永乐初年,有所谓“永乐初奉诏校大藏经”[15],然而,何时开刻,何时完成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至迟在永乐十七年(1419)之前已经全部完成,因为这一年《永乐北藏》已经开刻了,而《永乐南藏》是《永乐北藏》的主要校本。如上所述,《永乐南藏》改变了之前大藏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的排序,改成大小乘经,大小乘律,大小乘论这样的排序,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而后《永乐北藏》、《嘉兴藏》及清《龙藏》相互影响的关系都有明确的记载,从而成为关系较为紧密的一种系统。
我所概述的至清《龙藏》我国历代大藏经的四种系统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实际,只是一种个人的看法。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查阅了大陆版《中华藏》几种大乘经的校勘记,其中的一些资料作为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种体系的划分。
1.《放光般若经》,见《中华藏》第7册。
① 卷1,这卷经的前三条校勘记的内容是:“一此经卷数金、丽为二十卷,石、资、碛、普、南、径、清为三十卷;一一页上一行“放光般若经”,石作“放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资、碛、普、南、径、清作“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以下各卷同;一一页上二行译者,石作“西晋沙门无罗叉共竺叔兰等译”,资、碛、普、南、径、清作“西晋三藏无罗叉共竺叔兰译”。以下各卷同。
这三条校勘记如果简单地作出推论,它可得出《放光般若经》在诸版大藏中可区分出3种版本,一是《赵城藏》、《高丽藏》为代表的一个版本;一是以《房山石经》本为代表的一个版本;其他宋元明清诸大藏经本为一个版本。
② 卷2,这卷经涉及文字校对的校勘记共58条(首尾2条为说明文字),其中资、碛、普、南、径、清作为共同内容的一组,与底本不同的校记多达32条,如:“三○页中六行第二字‘相’,资、碛、普、南、径、清作‘想’。下同至页下九行第三字”;“三一页下末行第九字‘何’,资、碛、普、南、径、清作‘贪’”;“三二页上一二行 ‘不出’,资、碛、普、南、径、清作‘不出生’”。
③ 卷3,如上述,在全部58条校勘记中,资、碛、普、南、径、清作为一组与底本不同的校记占34条;其他出校的情况是:石5条,资5条,丽6条,石、普、南1条,普、南、径、清2条,资、径、清1条,石、普、南、清1条。举例如:“三一页中末行末字‘习’,资、碛、普、南、径、清作‘集’”。
《放光般若经》其他各卷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比如:
卷4,在62条校勘记中,资、碛……径、清一组的校记有31条;卷5,在52条校勘记中,资、碛……径、清一组有20条;卷6,99条校勘记中,资、碛……径、清一组有31条,此卷中碛独立出校者达20条;卷7,72条校勘记中,资、碛……径、清一组有27条,等等。
2.《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4卷,见载《中华藏》第9册。
卷1,此卷前二条校勘记是:“一底本,金藏广胜寺本;一此经底本与丽藏本分为四卷;石、资、碛、普、南分上下两卷;径、清分上、中、下三卷。”此卷涉及文字内容的校勘记共51条,资、碛……径、清作为一组出校勘记有25条。其他各卷大致相同,不一一罗列。
3.《佛说阿弥陀经》2卷,见载《中华藏》9册。
此经卷上的前三条是:“一 底本,金藏广胜寺本;一 五五二页中一行经名,底本原作‘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 资、碛、普、南、径、清、丽作‘佛说阿弥陀经’;一五五二页中二行‘月支国居士’,石、南、径、清作‘月氏优婆塞’;资作‘月支’。下同;碛作‘代月支国优婆塞’。”
此经卷上涉及文字校勘的校勘记共133条,其中资、碛……径、清一组出校的有48条;碛独立出校的有29条。卷下大致相同。
以上例举的这些情况,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参考。
①《金藏》、《高丽藏》与宋元明清诸版大藏有着一定的不同,这不仅反映在分卷上,经名上,译者的标注上,也反映在经文内容中。
②宋元版与明清版大藏经虽然可以划分为两个体系,其主要表现是在经籍的排列顺序上;如果从经文内容上说,它们比较接近。这说明,宋元以来的诸版大藏经都是在福州版大藏经的影响下一脉相承下来,它们的袓本就是肇始于《崇宁藏》的,在福州地方流传的以《开元释教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
③中国历代大藏经总的说可以区分出四个大体相近的类别。但这种类别的划分是相对的,只反映它们在总体上的某些差别,比如所据底本不同,版式不同,内容的某些差别等。但这种差别也只是一种版本上的差别,即大藏经在流传过程中,抄写形式的变化,抄写的错讹以及主持刻藏者的某些小的改动等,这些都不影响大藏经作为佛教经典总集的性质和它们其本相同的内容。
④在同一类型中的几种藏经版本,也不是一模一样,它们也有优有劣,比如《碛砂藏》与同时代或早或晚的大藏版本比较,它可能是差错和改动较多的一种版本。比如在《佛说阿弥陀经》卷上的一卷经中,碛单独出校就多达29条,就是说在29处,《碛砂藏》本发生了差错。比如“五五二页中五行一一字‘智’,碛无。”原文是“贤者拔智致”。诸本同,而《碛砂藏》作“拔致”。又如:“五五二页中一九行末字 ‘念’,碛作‘惟’”。原文是“佛坐息思念”,诸本同,而《碛砂藏》本作“佛坐息思惟”。而属于同一体系的其他藏经也有差错,只不过少一点。
三、汉文佛教大藏经几种体系形成的原因
历代大藏经体系的形成,大体上有如下几种原因,一是时代的原因,一是地区的原因,一是所据底本的不同。但归根到底还是与当时某一地区流行的一种与官方有关的官写本大藏经有直接的关系。
如上述,《开宝藏》是北宋初年敕命在益州(成都)雕造的。为什么不在中原中央政权所在地,而要在远在西南边地的四川去雕造藏经呢?这与当时时代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五代短短的53年中,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改了五次国号。当时是以兵战为务,频繁的战争,使得中原的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而就文化说其境况更是可想而知,如《宋史·艺文志》载:
“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苦,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16]
在这种形势下,佛教典籍的命运可能更惨。这就是为什么在宋太祖开宝年间敕命在成都书写金银字大藏经“数藏”[17]的原因,因为在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佛教的写本经籍可能已荡然无存了。这也是之后又敕命在成都雕刻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的原因。
《开宝藏》刻成后,经板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运抵京城开封,太宗命于太平兴国寺建印经院开始印藏。《开宝藏》作为一部官版大藏经,它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就是敕命在成都书写的金银字大藏经。这种官写本金银字大藏经有着自己的特点,也因此形成了《开宝藏》的版式风格和内容特色。从记载中知道,《开宝藏》曾“严饰天下寺舍”[18],其影响在南方曾达到江浙地区,如《指要录》的作者就是在浙江金华山的智者禅寺阅《开宝藏》的[19];向北曾传播于山西,介休的空王院、西京资圣院及永福寺等都曾收藏过《开宝藏》[20]。另据现存《开宝藏》本《大般若经》卷206等的卷末的墨记,晋南的福严净影寺(今青莲寺)僧在宋徽宗大观年间(1108年前后)请印过一部《开宝藏》。在金朝统治时期,晋南百姓很可能就是依据这个印本覆刻了《金藏》。《开宝藏》经板可能毁于宋金战争,现在除《赵城金藏》和《高丽藏》外,我们还不知道有哪部大藏经与《开宝藏》有直接的关系。《开宝藏》在中国的刻藏史上虽地位崇高,但影响并不是最大。
《契丹藏》亦如是。《契丹藏》诞生于宋辽对峙之时,是依据流行于幽州地区的一种官写本大藏经刻造的。《契丹藏》刻成后,我们除知道它曾多次传入高丽外,不见其在中原及江南地区的传布。这可能与当时宋辽对峙的局势有关,这也使它成为一种比较孤立的版本,后来几乎被人遗忘,并散失殆尽,要不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两次发现,我们至今还难识其真面目。
应该说,在中国大藏经史上,影响最大的还是雕刻于福州的两部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在这个边远的地区,因为地方割据势力闽王王审知笃信佛教,在福州造塔写经的偶然事件,留下了一种以《开元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这就为北宋后期福州东禅等觉院和开元寺先后刻藏创造了条件,也自此为中国佛教提供了一种新的大藏经版本。这种版本在南宋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客观形势下,直接影响了之后江浙地区私版大藏经的刻造。宋版《圆觉经》、《资福藏》,宋元版《碛砂藏》、元《普宁藏》及明初的《初刻南藏》都是福州版的延续,从而成为影响最大的一种大藏经体系。
在元朝世祖时代,曾下敕“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宋大藏圣教,名之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21]”。其目的是要为今后编刊大藏经提供一部权威性的目录,所谓“作永久之绳规,为方今之龟鉴”[22]。《至元录》在分类上的最大特点是突破了《开元录·入藏录》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的编排体系,而改变为大乘经、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的编排系统。《至元录》编成后已是元世祖的晚年,世祖来不及据之雕造大藏经就去世了。元大德年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将其“刊入大藏”[23],也就是续补刊入实际已完成的《碛砂藏》和《普宁藏》,由此造成对后世的影响。到明《永乐南藏》雕刻时,就据之改变了经籍的编排顺序,并第一次以正藏的内容将《至元录》收录藏中。之后的明清版大藏经均依《永乐南藏》的体例,从而形成了大藏经的又一个体系;但在经籍的内容方面则依然受到福州版的影响,使它们之间成为一种比较接近的版本。
通过上面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到,大藏经每种体系的形成,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都与当时某一地区与官方有关的某种官写本大藏经或大藏经目录有关,而依据这种官写本大藏经或受到如《至元录》这种奉敕编撰的大藏经目录影响而雕造的大藏经就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我的这种略显简单的分析只是一种个人的看法,请专家指正。
注文:
[1]徐时仪《金藏、高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渊源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2期18-31页。
[2]小野玄妙着,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870-918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3]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145-146页及153-156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4]《指要录》全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是宋初名僧惟白阅《开宝藏》而撰着的一部提要性着作。
[5]《指要录》卷8,《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768页。
[6]吕徵《宋刻蜀版藏经》,《吕徵佛学论着选集》卷3 1430页,齐鲁书社1996年版。
[7](辽)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序,《影印高丽大藏经》41册785-786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版。
[8]《山顶石浮图后记》,录文载《房山石经题记汇编》11-12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78年版。
[9]方广锠 《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240-2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5,《中华佛典集成》第9册155页,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11]文载《全唐文》825卷,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册8698页下。
[12]文载《全唐文》825卷,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册8692页下。
[13]此记云:“又,王审知泥金银万余金,作金银子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旃檀为轴,玉饰诸末,宝髹朱架,纳龙脑以灭蠹蟫”。转引自笔者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199页。
[14]《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
[15]《释氏稽古略续集》卷3,《大正藏》卷19942页。
[16]《宋史》卷202“艺文志”序。《二十五史》第7册636-6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7] [18](唐)神清撰《北山录》卷10,《大正藏》卷52。
[19]《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771页。
[20](宋)文彦博《永福寺藏经经记》,文载《介休县志》卷9。
[21] [23]释克己《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179页。
[22]《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1庆吉祥撰前言,《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180页。